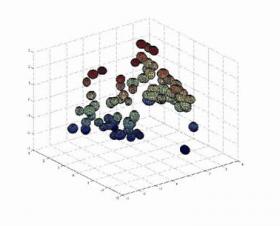摘 要
镜像神经元作为近二十年来神经科学领域内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相关的一系列研究掀起了一场“理解社会行为的革命”。然而,通过系统考察镜像神经元最初的操作性定义、基本功能及其实验证据,发现许多研究者对于镜像神经元的定义存在误解,人类脑中是否存在镜像神经元及其功能依然是当前学术界的争议焦点。迄今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就是、、以及的直接神经机制。因此,将镜像神经元视为“认知科学的圣杯”的主张是一种落后的模块论意识形态,只能催生新的“神经神话”。
关键词 镜像神经元 动作理解 动作模仿 共情 读心 模块论
1 引言
近二十年来,镜像神经元及其相关研究正在横扫神经科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临床医学,并逐渐渗透至哲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而建构起一张无比巨大的交叉学科网络。自发现镜像神经元起,研究者不断提出其可能在人类认知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包括诸如动作理解、模仿、共情以及心理理论等多种关键的社会认知功能(Gallese et al., 2011)。更有不少学者大胆预测其是语言进化、心灵感应( telepathy)、美学欣赏、药物上瘾以及政治冲突与暴力色情传播的神经基础( Cook et al., 2014)。镜像神经元俨然成为了“认知科学的圣杯 ”,似乎所有认知与行为背后原先种种难以参透的奥秘,只要放置到这个圣杯之中,就能被旋即一一化解。
遗憾的是,镜像神经元及其研究领域内的争议之持久与激烈本身并不逊于该领域内所取得的研究进展。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研究几乎推翻了绝大多数之前对于镜像神经元功能及意义的猜想。这使得科学界开始反省之前对于镜像神经元的理解和认识(Hickok, 2009; Uithol et al., 2011)。毫不夸张的说,当前的研究已经逐步将镜像神经元请下了“科学神坛 ”。本文尝试从镜像神经元研究中的争议出发,借助对其定义、理论假设与实验证据的分析,力图厘清这些争议的表现形式及其认识论根源,最终破除视镜像神经元为“认知科学圣杯”的“神经神话”(Neuromyth)。
2 镜像神经元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何谓镜像神经元?人类脑中是否存在着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或系统)的功能是什么?这三个问题被牢牢地被绑定在一起构成了诱发相关争论的“导火索”,而无视这些争论直接导致了上述误解。
2.1 镜像神经元定义的澄清
有关镜像神经元的操作性定义需要从最初的研究文献中予以澄清。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帕尔玛大学的神经科学团队利用单细胞记录技术在豚尾猴的腹侧前运动区皮层( ventral premotor cortex,VPM)(F5 区)与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IPL)(PF/PFG 区)相继发现了一些具有特殊属性的视觉运动神经元( visuomotor neurons)。这些神经元不仅在豚尾猴执行有目的的动作( goal-directed action)(比如抓起一粒花生,把它送到嘴里的过程)
时被激活,也会在猴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下,观察其他个体做上述动作时被激活( Casile, 2013)。之所以称其为“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是因为“脑将知觉到一个动作这一意象投射到了运动系统中,后者会通过即时的、自动化的加工,产生一个对相同动作的运动编码。就像镜子可以对直接感知到的意象产生一个精确的拷贝”(Williams, 2013)。
Rizzolatti认为,镜像神经元之所以引起神经科学界如此的轰动,是因为它用一种极其直观明了的机制解释了人类社会认知中最基本但又最神秘的功能:个体和他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之前的理论认为:负责个体自身运动的表征和感知他人运动的表征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他人动作的信息在被感知后需要经过复杂的推理思考才能对应上自身的运动表征库,从而达到对他人动作的理解。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则表明:( 1)感知他人动作的过程和匹配自身运动表征库的过程可以发生在同一个神经元层面上;(2)个体对他人动作的理解不是借助复杂的思考推理,而是通过自身的运动表征库去模拟解析他人的动作(Grafton, 2009)。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随后引起了整个神经科学界的轰动,但纷至沓来的却是不少研究者对镜像神经元这个特定名词的误用和滥用。作为发现者之一, Rizzolatti(2004)在迄今为止镜像神经元领域内最重要的一篇综述中明确指出了镜像神经元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特征:( 1)镜像神经元必须是运动神经元,即在个体执行动作时会放电;( 2)除了自身执行某一动作时放电,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还必须具备感觉 -运动的对应。即在观察到他人执行相似动作时也放电。例如,几乎所有镜像神经元在对视觉(其中一部分涉及听觉)运动的反应与其编码的运动反应方面呈现出一致性。需要注意的是,遵循上述操作性定义, Kilner和 Lemon(2013)对 1992年以来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 25个原始实验报告进行了分析,确认了猴脑中存在镜像神经元的主要脑区有两个:顶下小叶的喙部( rostral IPL)(即 PF/PFG区)和腹侧前运动皮层(即 F5区)。并且,F5区中镜像神经元平均比例只占所有神经元的 30%左右,IPL区中的镜像神经元平均比例只占所有神经元的 15%左右。
2.2人脑中有无镜像神经元的争论
人脑中是否存在镜像神经元是目前该领域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 Cook et al., 2014; Dinstein et al., 2008)。虽然一系列收敛性证据均指向人类大脑中的确存在着镜像神经元的可能性,然而在获取确凿的证据方面却一直停滞不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由于实验伦理的限制,研究者不可能在人脑中疑似存在镜像神经元的皮层中任意设置微电极来采集单个神经元神经电生理活动。因此,目前一般采用 PET、fMRI等非侵入性的脑成像技术来检验人类在执行与观察目标导向动作过程中所激活的脑区是否存在着空间上的重叠部分,借此间接地推测这些脑区中是否存在着镜像神经元。借助上述方法,研究者发现在人类大脑的顶下小叶的喙部(IPL)、中央前回( precentral gyrus)的底部以及额下回( IFG)的后部在功能上具有类似猴镜像神经元的视觉 -运动对应特征,而这些区域也是人脑进化上和猴脑镜像神经元同源的脑区,因此上述区域也被视为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 mirror neuron system)(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然而, Turella 等( 2009)对 33个支持人类大脑中存在镜像神经元的脑成像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统计学上的分析。结果显示,如果以观察动作与动作执行过程中都会激活的脑区作为可能存在镜像神经元的脑区,只有 5个研究符合这一标准,且这 5个研究中发现的那些同时在观察与执行动作时激活的脑区依旧不一致。这意味着研究者在人类哪些脑区可以算作镜像神经元系统上并未达成一致。
其次,伴随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运动皮层之外的脑区被发现呈现出镜像属性,这促使研究者开始反思之前脑成像方法学上的缺陷是否导致了无法准确确认并定位人脑中的镜像神经元(Molenberghs et al., 2012)。一些研究者开始使用目前最先进的脑成像研究手段—— fMRI 重复刺激范式( repetition suppression paradigm)来准确定位镜像神经区域,并发现不少区域具有镜像特征(Hamilton & Grafton, 2006)。接下去,又有研究者改进了实验设计来排除在 fMRI重复刺激范式中假阳性结果的可能。他们认为,之前的研究仅仅通过确认单一重复抑制现象( umRS)就试图推测其存在镜像神经元是不够严谨的——因为在严格遵循镜像神经元的操作性定义下(即同时编码自身动作的运动表征和他人动作的视觉表征),一个可能存在镜像神经元的皮层区域不仅应该表现出单一重复抑制现象,还应该表现出交互重复抑制现象( xmRS)。在上述实验逻辑的指导下, Kilner 等(2009)在区域分析中发现只有人脑额下回中的一小个区域出现所谓的交互重复抑制现象; Chong等(2008)的实验中则只在顶下小叶中的一个区域发现了“类似”的交互重复抑制现象,但是不对称的交互重复抑制现象(先执行再观察动作时有抑制现象,而先观察再执行动作时则未出现抑制现象),暗示着这部分脑区没有完全符合镜像神经元的标准。 Lingnau等(2009)的实验中则未发现任何脑区出现对于动作刺激的交互重复抑制现象。这些结果表明,即使使用了更先进的脑成像处理方法、更精确的实验设计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证实人脑中存在镜像神经元。
再次,即便将来有研究发现运动皮层出现交互重复抑制现象,还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囿于空间分辨率的成像技术无法进一步确定在有效执行与观察动作过程中都有激活的三维像素点( voxel)中的神经元是相同的。即使是再小的三维像素点也包含了上千个神经元细胞( Gallese et al., 2011)。因此,即便是通过重复刺激范式检测而得到确认的脑区,依旧只能算是“假定的镜像神经元系统”( putative mirror neuron system)。
最后,虽然 Mukamel 等(2010)的研究首次使用单细胞记录技术对癫痫患者脑中是否存在镜像神经元进行了检测,并发现在癫痫病灶附近的部分脑区中存在类似“镜像活动”属性的神经元。然而,由于该实验仅仅是癫痫治疗的附属研究,故而只能在经典镜像神经元系统之外植入电极,且最终发现的“镜像活动”属性也不符合 Rizzolatti给出的镜像神经元操作性定义。因此,该研究远非该领域的“判决性实验”( crucial experiment),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Casile, 2013; Welberg, 2010)。
2.3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功能的争论
相比于人脑中是否存在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功能的确定所引起的质疑和争论更为激烈。在镜像神经元发现之初,由于其独特地将编码自身相关的表征和编码他人类似信息的表征合为一体,一些科学家大胆地预测镜像神经元是人类许多社会认知的基石( Cook et al., 2014)。然而,“在镜像神经元研究走过二十年的历程后,各种证据表明简单的镜像机制( mirroring mechanism)不足以解释过多的人类社会知觉、认知与互动过程”( Kessler & Garrod, 2013),似乎没有任何一项社会认知功能完全依赖于镜像神经元(或系统)。
动作理解可能是镜像神经元研究者最初也是最保守的猜想(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它具体指的是,镜像神经元能通过在自身运动库中动作信息的匹配来模拟观察到的他人的动作,从而获得对他人动作的理解,是模拟论( simulation theory)的一种。然而,不仅有方法论者质疑当初猴脑中发现镜像神经元的电生理学方法的科学性( Dinstein et al., 2008),还有认知理论学家认为目前的实验证据无法充分证实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具备动作理解的功能(Borg, 2007; Hickok & Sinigaglia, 2013)。首先,之前的研究发现猴对动作的理解可以不通过激活镜像神经元系统而实现( Uithol et al., 2011)。其次,即使猴脑中镜像神经元是猴动作理解的基础,直接将猴镜像神经元的功能推广到人脑中也是欠科学的(Hickok & Sinigaglia, 2013)。不少研究发现猴镜像神经元的属性和人类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属性不完全相同。比如,猴镜像神经元仅仅编码有目的的动作(即及物动作)。然而,人类镜像神经元还编码许多不及物动作( intransitive actions)以及手势,对于这些动作的理解牵涉到的脑区远远大于镜像神经元系统( Hickok, 2009)。再次,无论猴脑镜像神经元或人脑镜像神经元系统都只能对熟悉的动作发生镜像反应,而对于新奇的动作则需要其他非镜像神经元脑区的激活( 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10)。最后,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不少研究都表明无论是用经颅磁刺激( TMS)暂时性地损伤镜像神经元系统,还是大脑损伤病人中缺少镜像神经元系统所在的皮层,抑或是通过特殊训练改变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活性,都无法使人类完全丧失对动作理解的能力( Hickok, 2009)。最近, Sinigaglia 和 Rizzolatti(2011)也出面澄清了镜像神经元和动作理解的关系:“虽然之前的证据表明了镜像神经元在动作理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证据不能理解为镜像神经元所参与的动作理解过程覆盖了所有的动作理解过程,更不能解读成动作理解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镜像神经元的参与。这些夸大的推论是没有实验根据的,也是违背我们当初解释镜像现象的初衷的。”这些不可忽视的矛盾点表明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在动作理解功能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除了动作理解之外,动作模仿也是猴镜像神经元发现者们最初提出的两个功能之一( Rizzolatti & Craighero, 2004)。然而讽刺的是,至今为止研究者无法证实猴具备模仿能力,所以猴镜像神经元不太
可能是动作模仿的神经机制( Hickok, 2009)。其次,从认知过程上来说,人类的模仿行为包含了模仿( unconscious mimicry)和有意识模仿两大类。前者指的是在社会交流活动中人们自动化地复制他人的动作、姿态、言语和表情。诸多研究表明,镜像神经元系统是无意识模仿的神经机制(汪寅等 ,2011)。区别于无意识模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描述的模仿概念主要指的是有意识模仿,即人类在获取语言、技能和文化时有意识、有目的的学习他人行为的认知过程。虽然之前脑成像研究发现镜像神经元系统在有意识模仿任务中被激活,但进一步研究表明有意识模仿所需要的脑区远远超过镜像神经元系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前额叶区域( PFC)。具体来说,研究者发现前额叶选择性地对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抑制和调控是有意识动作模仿的关键(Heyes, 2012)。因此,镜像神经元(或系统)至多是有意识模仿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共情以及读心也是很多研究者所宣称的和镜像神经元密切相关的社会认知功能。例如,曾红等(2013)认为:“由于镜像神经的功能,观察者……充分感知到他人产生动作时的身体动作及其所隐含的意义,并产生外在或内隐的行为模仿,或使人们对观察到的、动作有‘感同身受’的体验,从而达到理解行为、的目的。”虽然最初在猴镜像神经元上的研究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情绪和意图的内容,但一些研究者认为镜像神经元也可以通过类似动作理解的模拟机制来帮助个体获知他人情绪以及思想意图。然而,这样的推论显然是过于简单的(Borg, 2007)。首先,模拟论哲学家质疑镜像神经元在共情过程中的放电活动与模拟论的定义不相符(Gallagher, 2007)。其次,共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认知层面上来说主要分为情绪共情( emotional )和认知共情( cognitive empathy)。尽管一些脑成像方面的结果显示镜像神经元系统在一般的共情任务中被激活,但最新的研究却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共情过程都依赖镜像神经元系统。镜像神经元系统可能只参与了情绪共情的过程( Shamay-Tsoory et al., 2008)。最后,镜像神经元系统并不是共情和读心过程中惟一被激活的脑区。比如,在共情的过程中,脑岛,前扣带回( ACC)和杏仁核等的活动对共情的发生至关重要( Lamm et al., 2007)。在读心过程中,中前额叶( MPC)和颞顶交接( TPJ)的活动甚至比镜像神经元更为重要( Frith & Frith, 2012)。
3 总结
综上,镜像神经元(或系统)所具有的功能属性并没有像许多研究者所宣扬的那样神奇:“人类的概念形成、语言理解、共情、模仿等心智过程都与镜像神经系统的功能有关”(叶浩生 , 2013)。由于之前相关的实验证据或多或少的在方法学以及结果解释上存在争议,故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就是动作理解、动作模仿、共情以及读心的直接神经机制。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在上述四个认知过程中至多扮演了一个必要而不充分的角色。镜像神经元(或系统)功能的阐明还远远没有解决( Gallese et al., 2011; 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10)。最后,如果说上述四个功能还有相关实验证明有镜像神经元(或系统)的参与,那么余下那些被假设的镜像神经元的认知功能则完全是一些理论学家纸上谈兵构建出来的猜想,无任何实验的证据。
然而,为什么镜像神经元会被许多研究者奉为“认知科学的圣杯”?关于其的功能则被渲染成一个新的“神经神话”?这种现象背后显然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认识论因素。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许多“空头理论家”( theologians)还处于落后的模块论( modularity)意识形态中。受过去 19世纪颅相学的影响, 20世纪裂脑的研究,以及近十年媒体对于左右脑认知功能分管的鼓吹,许多学者还停留在某个脑区负责某个认知功能的脑模块论理论中,这就使得如此多的认知功能“被”赋予镜像神经元。然而,最新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大脑是一个整合的神经网络,任何认知功能都是建立在神经网络的动态变化中而非单一的脑区或某类神经细胞的放电。虽然说镜像神经元在许多认知任务中被激活,但是这并不表明镜像神经元是该认知功能所必需的神经机制。相反,镜像神经元可能只是大脑对于外界动作信息解码的众多过程中的某一步,而动作的理解、模仿、共情、读心则需要更多的社会脑( social brain)的参与( Hickok, 2009)。正如神经哲学家 Churchland(2011)总结的:“镜像神经元只是一个神经元,尽管可以在功能上是复杂的,但仅仅是一个神经元而已,并不是缩小的智慧侏儒(intelligent homunclulus)。”
因此,研究者必须抛弃将认知科学内诸多研究主题“毕其功于一役”于镜像神经元的粗犷思维模式,将众多认知过程贴上“镜像化”( mirroring)的标签只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未来的需要从镜像神经元(或系统)的基本功能入手回答如下问题:
(1)自主体( agent)如何将自己与他人的动作意图有效的区分开来?在通常情况下,无论是豚尾猴还是人类都不会将两者混淆。由此衍生的动作模仿、共情以及读心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研究者必须进一步考察镜像神经元系统与其它社会脑区域如何在上述认知活动中相互协作与制约。( 2)动作理解是由具身模拟( embodied simulation)还是推论式推理(inferential reasoning)实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外部情境因素如何影响动作理解。例如,我们观察到他人的抓取动作,可以激活自身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去理解动作的目标。但这个抓取动作的结果是什么并非是由动作本身决定的,而是完全取决于非运动的情境(例如,抓起杯子喝水、清理或闻香味)。已有许多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虽然也考虑到了情境因素,但却将动作理解的实现归因于由镜像神经元(或系统)激活的非推理与计算性质的具身模拟。正如 Hickok(2013)质疑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必须先推理处于情境之中的动作目标,然后才能如具身模仿论设想的去激活相应的动作链从而理解动作目标。换言之,推论式推理即便不能完全取代也至少先于具身模仿。这种基于情境的动作目标推理在神经机制上与镜像神经元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待继续追问。
参考文献
汪寅, 臧寅垠, 陈巍. (2011). 从“变色龙效应”到“镜像神经元”再到“模仿过多症”——作为社会交流产物的人类无意识模仿 .心理科学进展 , 19(6) , 916-924.
叶浩生 . (2013).认知与身体 :理论心理学的视角 .心理学报 , 45(4) , 481-
488.曾红, 叶浩生, 杨文登. (2013). 镜像神经在药物心理渴求中的作用及机制 . 心理科学进展 , 21(4) , 581-588. Borg, E. (2007). If mirror neurons are the answer, what was the questio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4(8), 5-19. Casile, A. (2013). Mirror neurons (and beyond) in the macaque brain: An overview of 20 years of research. Neuroscience Letters, 540, 3-14.
Chong, T. T. J., Cunnington, R., Williams, M. A., et al. (2008). fMRI adaptation reveals mirror neurons in human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Current Biology, 18(20), 1576-1580.
Churchland, P. S. (2011). Braintrust: what neuroscience tells us about mor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ok, R., Bird, G., Catmur, C., Press, C., et al. (2014). Mirror neurons: From origin to func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37(2), 177-241.
Dinstein, I., Thomas, C., Behrmann, M., et al. (2008). A mirror up to nature. Current Biology, 18(1), 13-18.
Frith, C. D., & Frith, U. (2012). Mechanisms of social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3, 287-313.
Gallagher, S. (2007). Simulation trouble. Social Neuroscience, 2(3-4), 353-365.
Gallese, V., Gernsbacher, M.N., Heyes, C., Hickok, G., & Iacoboni, M. (2011). Mirror neuron forum.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369-407.
Grafton, S.T. (2009). Embodied cognition and the simulation of action to understand other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156, 97-117.
Hamilton, A. F., & Grafton, S. T. (2006). Goal representation in human ant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6(4), 1133-1137.
Heyes, C. M. (2012). Grist and mills: On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cultural learn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7(1599), 2181-2191.
Hickok, G. (2009). Eight problems for the mirror neuron theory of action understanding in monkeys and humans.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1(7), 1229-1243.
Hickok, G., & Sinigaglia, C. (2013). Clarifying the role of the mirror system. Neuroscience Letters, 540, 62-66.
Kessler, K., & Garrod, S. (2013). Editorial: Cortex discussion forum on “the meaning of mirror neurons”. Cortex, 49(10), 2603-2606.
Kilner, J. M., & Lemon, R. N. (2013). What we know currently about mirror neurons. Current Biology, 23(23), R1057-R1062.
Kilner, J. M., Neal, A., Weiskopf, N., et al. (2009). Evidence of mirror neurons in human inferior frontal gyrus.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9(32), 10153-10159.
Lingnau, A., Gesierich, B., & Caramazza, A. (2009). Asymmetric fMRI adaptation reveals no evidence for mirror neurons in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6(24), 9925-9930.
Molenberghs, P., Cunnington, R., & Mattingley, J. B. (2012). Brain regions with mirror properties: A meta-analysis of 125 human fMRI studies.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6(1), 341-349.
Rizzolatti, G., & Craighero, L. (2004). The mirror-neuron system. 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 27, 169-192.
Rizzolatti, G., & Sinigaglia, C. (2010). The functional role of the parieto-frontal mirror circuit: Interpret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s, 11(4), 264-274.
Shamay-Tsoory, S.G., Aharon-Peretz, J., & Perry, D. (2008). Two systems for empathy: A double dissociation betwee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empathy in inferior frontal gyrus versus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lesions. Brain, 132(3), 617-627.
Sinigaglia, C., & Rizzolatti, G. (2011).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Self and others.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0, 64-74.
Turella, L., Peierno, A. C., Tubaldi, F., et al. (2009). Mirror neurons in humans: Consisting or confounding evidence? Brain and Language, 108, 10-21 .
Uithol, S., van Rooij, I., Bekkering, H., et al. (2011). What do mirror neurons mirror?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4(5), 607-623.
Welberg, L. (2010). Mirrors, mirrors, everywher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1, 374-374.
Williams, J. H. (2013). The mirror or portrait neuron system-time for a more organic model of action-coding? Cortex, 49(10), 2962-2963.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ZD18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2014T70578)和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2013QN003)的资助。** 通讯作者:汪寅。E-mail: slzwy@msn.com
Are Mirror Neurons the “Holy Grail” of Cognitive Science?
Chen Wei 1, 2, Wang Yin3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2Center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Research, Zhejiang University, Hongzhou, 310028)
(3School of Psychology,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10003)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mirror neurons in the 1990s has led to excitement in 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Mirror neurons have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from specialists both in the scientific field and public media. More and more abilitie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these neurons; they are
even hailed for what they “do for psychology as DNA did for biology”. And a series of related studies have given rise to “a revolution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behaviors”. Mirror neurons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a wide variety of functions, such as action-understanding, imitation, empathy, theory of mind, language evolution, telepathy, self-awareness,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Mirror neurons are viewed as the “holy grail” of cognitive science.
The assumption that mirror neurons play a key role in social cognition is not without controversy, however. This review shows that the current data about mirror neurons are very mixed and that those studies that use weakly localized measures to examine the functions of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re hard to interpret. Firstly, some theorists misuse and abuse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mirror neurons. Mirror neurons are a class of visuomotor neurons activated by both the execution and the passive observation of object-related actions. Cells having this property were only found in macaques within the premotor cortex (area F5), and in the rostral part of the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PF). Secondly, the idea that mirror neurons exist in human beings remains controversial, although the human homolog of the 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 and the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IPL) can be seen as a classic human mirror neuron system.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mirror neuron research; it turns out that unless one can manage to evade all the ethical, technical, and procedural limitations imposed on human brain research, no complementary re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to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mirror neurons in the human brain convincingly with microelectrodes or any other technique operations at the neuronal level. Last but not the least, claiming the mirror mechanis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s of others does not imply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action understanding. Some of these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social brain are basic and cannot be ignored, relying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 given stimulus and its corresponding effect.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its mirror mechanisms cannot be used to account for empathy, imitation and mindreading or explain other social cognition phenomena. It is an outdated ideology as a modularity of mind.
The future study for mirror neurons must attemp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How can an agent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tention of self-action and those of others? And how can someone’s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other social brains cooperate in this processing? (2) How can an agent make an understanding outcome prediction of an action? It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action itself, but also o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action is embedded. Key words mirror neurons, action understanding, action imitation, empathy, mindreading, modularity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