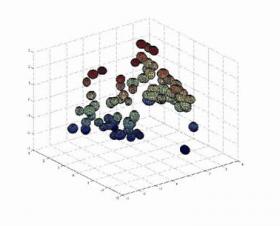与 ——科学新进路的哲学基础
作者:刘晓力 来源:《哲学研究》 日期:2005-10
为了避免认知科学中计算隐喻的局限,近年来建立在交互隐喻和涉身哲学基础之上的情境认知、涉身认知和动力学认知理论对传统认知观念进行了修正,这些新的研究进路揭示了认知过程的复杂特性,提出了对认知本质的新观念,为人们重新思考身心问题、心灵-大脑-机器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启示。
一、认知科学研究的新进路
事实上,在近40年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中,人们一直致力于思考人类认知的本质,破解主观的经验如何可能与可被客观描述的自然事件相关联这个“世界之结”。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在计算隐喻基础之上的经典计算主义逐渐暴露出局限性而受到挑战,一方面,如舒尔茨(M.Scheutz)等人在新的理念下提倡一种新计算主义的研究方向(2002);另一方面,人们一直在探索突破计算主义的新的研究进路。今天,可以说,认知科学中的计算主义在不断修正中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然而,理解认知本质的大一统局面也已经被多样性研究打破,许多学者从不同方向提出了一些理解人类认知的新理论。甚至有人认为,非计算主义的新范式业已形成,认知科学已经发生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van Gelder,1995,Lynn Andrea Stein,1999,p.1.)。
在新的研究进路中颇具影响的有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涉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动力学认知理论(Dynamicist Theory of Cognition)。其中,克兰西(W.Clancey)的《情境认知》(1996),布鲁克斯(R.Brooks)的《寒武纪智能》(1999)无疑是情境认知的代表作。瓦里拉(F.J.Varela)等人的《涉身心智:认知科学和人类经验》(1991)、克拉克(A.Clark)的《此在:重整大脑、身体与世界》(1998)、拉可夫和约翰逊(G.Lakoff&M.Johnson)的《体验哲学:涉身认知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1999),以及多罗西(P.Dourish)的《行动何在:涉身交互的基础》(2001)等倡导的涉身认知被看作“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的新方向;而格罗布斯(G.G.Globus)(1992),罗伯特森(S.S.Robertson)(1993),西伦(E.Thelen)和斯密斯(L.B.Smith)(1994)的动力学研究则标示着另一进路,特别是冯·盖尔德(T.van Gelder)和波特(R.Port)在《认知科学的新进路:认知的动力学说明》(1995、1998)中,明确提出将动力学范式(Dynamicist Paradigm)与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并列为认知科学的第三种竞争范式。所有这些新的研究中都包含着对传统的计算隐喻的质疑,包含着对符号、表征(representation)、计算和规则核心地位的反思,都包含着对认知主体如何与环境交互作用,如何通过感知-思维-行为介入世界等给出新的说明。更重要的是,各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进路都借助了某种包含基本哲学假定的隐喻,反映着不同哲学传统的内在影响。
二、新计算主义:重新理解“计算隐喻”?
传统认知科学中至为重要的哲学基础是功能主义假设和计算隐喻,这种假设将人和其他有机体的认知看作通过输入输出符号进行信息处理的功能,把人类心智比喻为计算机,强调“认知的可计算性”。不可否认,这种观念曾经极大地推进了认知科学以及关于认知科学的哲学解释,导致了对认知的物理的(physical)、符号的(symbolic)和语义的(semantic)三个层次的说明。
但是,计算隐喻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计算的实现必须首先完成客观对象的形式化过程。这就必然会遇到三个问题,(1)要使非形式化领域向形式化领域转变这一过程本身形式化将造成回归现象;(2)即使已经形式化了的问题还必须是可计算的,即必须存在解此问题的算法;(3)利用算法可解的问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计算复杂性,但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是所处理的问题类本身固有的性质,并不依赖于任何计算模型。以计算隐喻为基础的“思维-认知-信息处理-算法实现”这种自上而下的实现框架无法超越可计算性理论设定的技术界限。于是,认知科学家为了回避客观世界形式化的困难,转向大脑信息处理功能的形式化并寻求人类心智的算法可解性。即使这样,仍然不可回避如下难题:(1)大脑功能是否可描述为信息处理活动;(2)大脑的信息处理活动是否与思维功能直接相连;(3)大脑信息处理程序的初始状态是什么;(4)如何将模拟大脑信息处理的程序与周围环境相联系?此外,恐怕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是,当认知科学家回避了把客观世界形式化的困难而代之以人类认知功能的形式化,并且相信存在描述这种功能的计算层次时,他们还假定了所有计算状态的可物理实现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讲,也许在计算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可以建立其功能对应,但对于人类心智状态和其他物理状态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功能对应,我们目前并不清楚。针对这一系列困境,舒尔茨在其主编的《计算主义:新的研究方向》中倡导“基于虚拟机的新计算主义方向”,提出“人类心智状态是虚拟机状态”的假设,强调了具有构架(architecture)的系统中不同组件的交互作用是其核心所在。于是,在这一假设框架下,心智状态和认知过程可用虚拟机的“交互作用机制”给出说明。(M.Scheutz,2002)从舒尔茨以虚拟机的概念框架对于认知的新说明中,我们看到了新计算主义从关注“可计算性和算法”转向了关注系统构架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事实上,在此之前,斯坦尼(L.A.Steind)在《挑战计算隐喻》中就已经指出,由于今天的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更加关注涉身性、关注主体和行为,因此,传统的“计算隐喻已经被交互隐喻所取代”。(Lynn Andrea Stein,1999)。那么,“交互隐喻”对于认知实践的说明是恰当的吗?这种交互是在什么情境中发生的?“交互隐喻”对于“抽象符号如何获得实在世界的意义”等经典问题是否作出了实质性回答?
三、情境认知理论中的“交互隐喻”?
新计算主义关注焦点的转移除了一些不可克服的理论内部的困境外,其外部动力至少还来自像情境认知和涉身认知等其他非计算主义研究进路的挑战,这些研究在认知科学的不同领域,如、人工生命、机器人理论、认知和心灵哲学中都或多或少得到了体现,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个丰富的交叉科学研究领域。机器人学权威布鲁克斯在《没有推理的智能》和《没有表征的智能》(1991)中提出,以现有的计算机理论体系结构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没有反映生物系统的智能,人和其他动物是通过学习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并使其更好地适应环境来认知的,因此,我们应当沿着进化的阶梯自下而上地探寻智能的源头。“当我们研究了非常简单的低等智能时,发现关于世界的清晰的符号表征和模型事实上对了解认知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这表明最好以世界本身作为模型”。(R.Brooks, 1999,pp.80-81)他期望建造与人类共存于世的人工造物(系统),它们是完全自主的能动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通过控制整个系统的不同层次直接与环境作用,在其动力环境中可以随机应变地恰当处理问题,有适应环境和利用偶发环境调节自身行为实现多种目标的能力。布鲁克斯还概括出了理解认知的四个关键概念:(1)“情境性”(situatedness),指认知主体处在直接影响它们行为的情境中,其行为是靠具有动态结构的目标驱动的,完全不需要涉及抽象表征;(2)“涉身性”(embodiment),认知主体利用驱体、感知器官、视觉系统等进行认知,他们有来自周围环境的直接体验,其认知行为是涉身的;(3)“智能”(intelligence),智能的来源不限于计算装置,还来自周围情境、来自[机器人]多感应器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4)“突现”(emergent),智能是由系统的多部件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与环境交互作用所突现出来的总体行为。(R.Brooks, 1999, pp.133-186.)
由于传统人工智能的核心观念和方法主要来源于笛卡儿身心分离的思想遗产,他们假定心灵的功能是可由清晰的支配符号的规则解释的,因此其核心要素包含表征、形式化和基于规则的符号变换,认知被理解为基于清晰的形式化规则操作抽象符号表征的活动。按照情境认知理论,以这种“抽象符号表征隐喻”说明认知其缺陷在于,它使符号加工的内在场所、符号的意义世界、主体行为所涉之外部世界三者相互分离,也排除了对敏感性心智内容加工的可能性。显然,情境认知理论对传统人工智能的修正恰是企图通过倡导动态性和相互关联性弥合感知-行为的鸿沟,而且不主张在心理状态与行为之间以各类抽象表征作为内部连接。这种突出情境性的模型,可称作“情境中的目标导向的与环境同步的行为模型”。正如布鲁克斯所描述的,“在本质上,我们是想建立一种以外在世界为中介,存在于感知与行动之间的恰当的有效调节的反馈机制。我们需要走出完全以抽象方式思考世界的藩篱,而代之以考察正常的行为过程,这种考察能积极地预先把握可达到目标的合适的物理环境,因为由感官输入所监控的主体行为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才是主动积极的。”(R.Brooks, 1999, p.109.)
此外,情境认知不仅强调认知中主体与高度结构化的环境的交互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一种第一人称视角。“我们看作心灵和智力的成熟的认知能力可能更像航海,而不是单纯的生物大脑的机能。航海是对一个包含个人、仪器装置和实践扩展的复杂系统有机协调突现出来的。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心理机能可能同样被证明是扩展的环境系统的特征,而人的大脑仅仅是这系统的(重要)部分”。(A.Clark, 1996, p.214.)这里我们看到,对认知过程的情境性说明把作为计算装置的心灵完全转变为了有机体内部及其与环境时实的,由目标驱动的交互作用,强调了在与环境作用中基于行为的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在我看来,这是以“交互隐喻”代替传统的“抽象符号隐喻”来说明认知的本质。
四、认知的“涉身性隐喻”?
自1995年以来,与情境认知同行的非计算主义者大都被列入涉身认知研究者的行列,或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情境认知是涉身认知理论的一部分。所谓涉身认知是一种对有机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认知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说明,强调“涉身”是认知的必要条件。哲学上,这种认知理论试图对心-身-世界之间的交互方式给予理论说明。涉身认知理论首先建基在如下经验性假设之上,“大多数实在世界的思维是发生于特殊的复杂的环境中,往往有着非常实用的目的,而且需要控制外界并利用与外在事物互动的可能性”。“因此,认知是一种高度涉身的、情境化的活动,甚至思维的存在应当首先被看作是行动的存在”(Micheal L.Anderson, 2004)。依照西伦的表述,“认知是涉身的,意味着认知是从身体与环境的作用中产生的,从这种观点看,认知依赖于某种类型的经验。它们来自具有特殊的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这些能力与形成、、语言和生命的其他方面的基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把心灵看作一台只涉及支配能够恰当表征世界的符号规则和程序的机械装置的认知观念完全相左”(Ester Thelen,2001)。一般来讲,涉身认知包含的核心假定大致可以概括为:(1)实时发生的全方位的行动是第一位的;(2)涉身的方式决定认知类型;(3)认知是建构的。涉身认知学者为这些假定提供了相应的研究(Monica Cowart, 2005)。因此,拉克夫、约翰逊对30年来认知科学的成果提出了三个总结性断言:(1)心灵本质上是涉身的;(2)思想大部分是的;(3)抽象概念大多是隐喻的(G.Lakaff&M.Johnson, 1999,p.5.)。
在涉身性研究学者眼中,“涉身”的概念不仅包括了以身体为基础的、具体的、定域性的和参与生活世界交互作用的稍窄的含义,还包含了如下更宽泛的含义(Micheal L.Anderson, 2004,3.):
(1)生理学的,“心灵本质是涉身的”不仅仅因为所有心理过程都是神经例示的,也因为我们的知觉和运动神经的独特之处对我们定义概念、合理推理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我们的意识器官、视觉系统等生理学设计对意识内容以及所有在其中出现的表征的结构都有着直接的影响,也预设了对高级抽象概念的生理界限;(2)进化的,认知主体的进化和理性的进化是涉身性的重要方面,“‘理性是进化的’这一发现完全改变了人类是唯一的理性动物的观念,理性不是区别于我们和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相反,理性恰好将我们与其他动物同时置于进化的连续统中”;(3)实践活动的,动态的主体与世界的交互引起主体的实践活动以及这种活动与思维、问题求解和符号变换之间的内在关联;(4)社会文化情境的,实践活动和与环境的交互方式本身既可以看作生存方式,也可以看作一种认知策略,也是作为中介的一般的认知方式。这种交互本身总是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被建构的。
可见,认知的“涉身性隐喻”也是“交互隐喻”之一种,只是更加体现了主体与世界交互的纬度,体现了生活世界的意义。“涉身是我们与世界交互并使其具有意义的特性,涉身不仅意味着身体例示,涉身交互就是通过与人造物交互来创造意义、操控并改变意义的”。(P.Dourish,2001,p.216.)同时还包含了对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的实践意义。
五、复杂系统认知理论的“突现隐喻”?
与涉身认知关联的沿着非计算主义进路研究认知的动力学理论则将认知活动看作复杂系统的突现(emergence)性质,这类理论的核心是所谓的“突现隐喻”。
布莱顿贝格(Braitenbeng)1984年就提出智能可能是从人工神经元部件的交互作用中“突现”出来的观点。协同学创始人哈肯(H.Haken)1996年在《大脑工作原理》中认为,大脑是一种具有突现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巨系统。1995年冯·盖尔德在那篇著名论文《假如认知不是计算,会是什么?》中提供了对于理解认知的“动力学假说”(Dynamicist Hypothesis),“自然的认知系统是某种动力系统,而且从动力学眼光理解认知是最好的[途径]。”(T.van Gelder,1995,p.347.)依照他的理论,认知科学传统范式对认知的理解最为要害之处是脱离了时间纬度,而大脑是随时与外界有信息交流的,“与其说认知过程是‘无表征的’,不如说是‘在某类非计算的动力系统中存在状态空间演化’的”。他利用状态空间、吸引子、轨迹、确定性混沌等动力学基本概念来解释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认知主体的认知过程,用微分方程组表达处在状态空间的认知主体的认知轨迹,通过对一定环境下的认知主体的思维和行为轨迹的分析考察整个认知活动,以动力系统模型揭示认知不是孤立的事件状态,而是一系列认知事件状态的过程这一本质。[①] 有人认为,在新一代联结主义观念指导下设计的人工神经网络就是某种非计算的动力系统,遗传演化和群体的非经典计算理论则是神经联结主义理论与动力系统理论的联姻。丘奇兰德和谢诺沃斯基(P.S.Churchland &T.Sejnowski)(1992)就曾指出,联结主义承诺的是“通过构架的低层神经网络的作用将能达到复杂的认知效果”,“突现性是以系统的某种方式依赖于低层现象的高层结果”,并且认为,“直觉过程是一种亚概念的(subconceptual)联结主义动力系统,它不接受完全的、形式化的、精确的概念层次的描述”,“用亚概念网络把自然认知系统看作是神经动力系统当是最好的理解。”
此外,艾德尔曼(G.M.Edelman)在《意识的宇宙》(1998)中也明确提出一种假设,认为意识是涌现于集群系统动力学的。他指出,对意识经验有贡献的神经元集群的某个子集必须既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又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艾德尔曼将这种随时间变化的神经元集群子集称为“动态核”,作为意识经验基础的神经过程就发生在这种动态核上。在研究脑的神经动力学时,艾德尔曼认为,有一种依赖于丘脑皮层网络和其他网络中信号循环传输的“再进入过程”,它是脑内相互联结的区域之间不断进行着的并行信号循环的相互交换,这种相互交换不断协调着这些区域在时空两方面彼此映射的活动。人的意识和心智活动是动态的达尔文过程,人类的认知活动是脑与身体以及环境交互作用时通过选取神经活动的某些分布模式实现的。(杰拉尔德·埃德尔曼,顾凡及译《意识的宇宙》,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9-11章)著名的裂脑研究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佩里(R.Sperry)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突现决定论”(Emergent Deteminism),认为意识是脑活动的突现特性,它与神经机制有关,但不能还原为脑的神经机制。产生自我意识的脑神经过程包括许多从简单到复杂的系统,而且高层系统控制着低层系统行为。1991年他又倾向于“突现的下向因果机制”说明:精神和意识是大脑的整体性质。在认知过程中,神经元事件可看成是嵌入在更高层次的因果现象之中。在大脑活动的因果链中,意识经验以不可还原的突现形式出现在大脑过程的较高层次上。这些突现的心灵实体不仅在认知水平上交互作用,而且,对作为组分的神经元的活动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仅靠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不可能对大脑功能作出完整的解释。统一的主观意图必定因果地控制每个脑半球的神经元的激发模式。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整个精神系统具有因果效力地控制着人的大脑行为。(斯佩里,2004-3)
复杂系统认知理论与传统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表征的不同理解。如前所述,在传统认知科学范式中大家似乎都默认着一个假定,“没有表征就没有人类认知”。然而,动力学者认为,一个动力模型应当是“无表征的”。(G.G.Globus 1992,Thelen and Smith 1996;van Gelder 1993,1995)智能行为是感知-动作同时协调的结果,感知-动作的神经结构和组织过程是在运动中创造的,是在不断激活、竞争选择和重新组合过程中得到的一种自组织机制,并不依赖于任何形式的表征和计算。冯·盖尔德认为“表征概念对于理解认知是不充分的一种诡辩式的东西(van Gelder,1993,p.6)。西伦和史密斯更直接宣称“我们根本无须建立表征”!(Thelen and Smith 1996,p.338)布鲁克斯认为,“在智能系统的建造中,表征是完全错误的抽象单元。”复杂系统理论对于计算主义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展示了人类认知行为的复杂特性,动力系统的描述对认知行为的连续性也提供了随时间变化的自然主义说明,甚至有人认为它是认知科学最具生命力的新的方向。但是,以复杂系统的“突现”代替“计算”,虽然包含了某种定量分析,但由于突现的机制不能完全刻画,在我们看来仍然不过是一种新的隐喻。
六、涉身哲学及其启示
认知的涉身性研究也许直接的起因是对传统认知理论中的计算隐喻进行修正,但其哲学是基于胡塞尔(E.Husserl)和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生活世界”的涉身哲学思想。
按照胡塞尔现象学观念:我们所谈论的世界与主观被给予的方式之间的相关性是先验的。这种先验的相关性就是事物之为现象的根本,事物必然与显现(即给予-接受活动的方式)或与对象-意向活动相关联。存在就是显现的存在和存在的显现。生活世界不是一个自在的世界,而是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世界,是具有人的意向性视域的现象世界。在我们能对世界反思和进行科学解释之前,我们已经处在对世界的经验中了,我们与世界有了涉身的意向性和生存的适应性。梅洛-庞蒂认为,世界整体绝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视域,这个视域将我们圈在里面,我们生活于其中,我与世界是扭结在一起的。世界是进入人的实践领域的世界。因此在生活世界中,我们需要从认识论理性的简单性回到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从身心分离的人回到涉身心智,回到涉身经验的人,从理论状态回到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世界就在里面,我就在我外面”。因此,知觉和心理的内在表征总是发生在情境中的,是由涉身主体在与世界持续有目的地打交道中建构出来的。
依照涉身哲学理论,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和范畴化(categorize)是基于我们的涉身认知方式能动地建构的。涉身认知的方式不仅制约了我们与世界可能的交互方式,特殊的涉身认知方式也决定了世界展现于我们的方式。事实上,某种环境特征是依赖于大量相关因素而重构的。例如,人类往往表现出目标定向的行为,从而能动地建构感觉运动方式用来表征那些与相继呈现出的目标定向有关的环境特征,依赖于有机体在环境空间中呈现任务的不同方式,相关的环境特征也是以不同方式被我们观察到的(Monica Cowart, 2005)。
这些哲学假定对传统认知理论关于心灵-世界的观念提出了深刻质疑。传统的认知理论一向认为,世界有一种预先给予的特征集,这些特征是可以“世界之镜”的形式得到表征的,对世界的理解首先表现为我们借助符号化的表征系统进行问题求解的过程;认知只是有机体在被动受限的进化环境中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因此,对于认知的本质可以完全于有机体的内在认知过程来理解。这种孤立的对认知的理解显然完全忽视了对认知发展的说明。而涉身认知理论认为,思想首先产生于有机体在其环境中的意向性行为能力,更确切地讲,意味着有机体通过控制自身环境并采取一定的行为,从而发展出一种基于感知和运动能力的对世界的基本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朝着更复杂的高等认知过程迈出的第一步,没有这些行为的实现机制就没有思想和语言的产生。
涉身哲学研究的一个鲜明的倾向是对西方传统理性观提出修正。如上来自认知科学的三大经验发现是企图终结两千年来关于理性的先验哲学思辩,根本上改变西方传统的理性观。因为,在他们看来,两千多年我们一直用理性来定义人类的本质,理性主义所推崇的一致性、确定性和完备性信念不仅确定了我们描述世界的方法,世界也同样成了这组信念所规范的存在,即一种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存在。于是,世间就如同理论规范所描述的那样,一切确实的事情都必须经思维的程序化论证才具有其合法性,以致存在的确定性还要由论证的确定性来保证。而涉身认知学者关于理性的立场则是:(1)理性并非如传统认为的是非涉身的抽象能力,而是源自我们的大脑、身体和亲历经验的本性;(2)理性是进化的,因为所谓抽象的理性是建立在较低级的的动物知觉和运动能力基础上并运用它们的推理形式的;(3)理性并非是先验意义上“普遍的”,它不是世界结构的一部分,它的普遍性是由于它已经成为被所有人普遍分享的能力,而使它得以分享的是以我们的涉身心智方式存在的公共性;(4)理性并非完全有意识,它通常是无意识的;(5)理性并非纯粹真实的,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隐喻和想象的;(6)理性并非不含情感色彩,而是涉及的。而且,这种理性观的转变也是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解的一种根本转变。(G.Lakaff&M.Johnson,1999,p.3.)
传统认知科学的基本哲学假定是身心二元论,研究的对象是认知个体的内部状态和过程,借助的手段是纯粹抽象的符号表征,研究方法是与有机体相分离的,但它的终极目标却是寻求普遍的支配人类认知的统一原则。与此相应的对于心灵的黑箱式的功能主义和“计算隐喻”曾深刻影响了科学的哲学说明;表征和计算的模式不仅极大地支配了认知科学的哲学和修辞学,也支配了认知科学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的实践。涉身哲学思想也许能够对于如何反思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提供新的启示;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认知与世界的关联提供一种新的说明,对于认识论中如何将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整合提供某种理论依据。但是,以涉身认知理论对涉身性如此广义的说明,要么使我们停留在与世界的涉身交互这样的模糊隐喻中,要么将心智降至社会-文化-历史情境中随时间变化的适应性能力,真的能够揭示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中纯粹先验自我的意义,从而破解“世界之结”吗?
如果把“情境”、“涉身性”、“交互作用”、“动力系统”和“突现”这些概念所反映的不同侧面关联起来理解,我们似乎看到一幅涉身认知的生动图景:认知是依赖于我们的有机体的“在世的存在”,依赖于我们不同的经验种类的,依赖于认知主体的语言、意向性行为和社会-文化-历史情境的。认知不是孤立的事件状态,是生活世界中事件状态的序列构成的过程,而这种过程是认知主体在涉身于世的交互作用中生成的。[②] 这样一幅图景无疑对传统认知理论提供了必要的反思和批判。但依我个人之见,符号表征隐喻也好,计算隐喻也好,甚至交互隐喻、涉身性隐喻和突现隐喻也好,都是对于人类认知的不同侧面的说明,如果认知并非如传统计算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人类头脑中的符号信息处理过程,那么,否认了表征的重要作用而只强调主体与世界的涉身交互的社会建构说在消解了一些理论疑难的同时,是否会因为其缺少必要的规范性其解释力大大下降呢?从已给出的计算主义和非计算主义基本假定的划分中,我们似乎看出,情境认知、涉身认知和动力学认知研究的进路有可能在这些新隐喻和哲学观念的引导下产生新的实践研究范式,甚或为科学理论的说明提供某种概念框架或理论规范,这些规范将对于我们的科学实践具有某种助探式功能。
但是,认知科学毕竟是一个不够成熟的学科,其实践过程中的困难还依赖于诸多学科的进展,也依赖于物理实现条件和经验的检验。事实上,至今对于人类是否按照符号和命题那样的精神实体来表征事物,心灵是如何运作的基本问题我们无法做出真正的裁决。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生物学和复杂性科学的成果为我们提供的事实仍然十分有限,计算主义和非计算主义者双方似乎都有强硬的支持证据。而重要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对认知科学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基础性假设既没有提供足够的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也没有对其展开充分的哲学论证。我们相信,只要人类对智能的本质,对心灵的本质没有获得完全的理解,认知科学还将继续走在探索新范式的道路上。新的研究主题将如何变化、与传统研究的区别何在,它们的哲学基础是什么,以及诸方案的内在协调性问题仍将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到实在论传统与现象学哲学传统的争论也将继续,人工智能的成败,甚至认知科学的成败并不能终止人类对自我本真意义的永恒的哲学反思。
参考文献
Micheal L.Anderson 2004,Embodied Cognition: A Field Guid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ww .elsevier com/locate/artint..
R.Brooks 1991, 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7:139-159.
R Blooks 1999, Cambrian Intelligence: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ew AI,MIT Press, Cambridge, MA.
P.S.Churchland and T.Sejnowski 1992, The computational brain. Cambridge, MA,MIT Press.
A.Clark 1998,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 The MIT Press.
Monica Cowart 2005, Embodied Cognition,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Eliasmith 1996, The third contende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ynamicist theory of cognition, in P.Thagard (ed) (1998) Mind Readings: Introductory Selection in Cognitive Science. MIT Press.
C.Eliasmith 2001, Attractive and In-Discrete A Critique of Two Putative Virtues of the Dynamicist Theory of Mind. Mind and Machines. 11:417-426.
G.G.Globus 1992, Toward a non-computation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4 (4):299-310.
G.Lakoff, M.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Basic Books,New York.
R.Port & van Gelder 1995, It’s about time: An overview of the dynamical approach to cognition Mind as mo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sther Thelen and Linda B.Smith 1996, A 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and Action. Cambridge,MIT Press.
T.van Gelder 1995, What might cognition be if not comput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91,345-381.
T.van Gelder & R.Port (eds.) 1998, Mind as mo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Scheutz (ed.) 2002, Computationalism : New Directions , MIT Press.
Lynn Andrea Stein 1999, Challenging the Computational Metaphor: Implications for How We Think, Cybernetics and Systems 30 (6).1-35.
F.J.Varela, E.Thompson & E.Rosch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斯佩里《寻求与科学相容的生活信念》载于《科学文化评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3.
(工作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Interaction Metaphor and Embodied Philosophy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Some New Approach to Cognitive Science
Liu Xiaoli
Abstract: To eliminat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computational metaphor, situated cognition, embodied cognition and the dynamic theory of cognition have revis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cogni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approach to cognitive scienc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metaphor and embodied philosophy reveal the complexities of cognitive processes, provide the new concept about the nature of cognition and the new enlightenment on reconsidering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mind-body and mind-brain-machine.
[①]冯·盖尔德等人曾分析了认知科学的几个动力学系统模型,它们包括(1)罗伯特森(1990)的循环原动力行为模型;(2)斯卡德(Skarde)和弗里曼(Freeman)(1987)借助复杂动力系统理论描述感受器官的神经系统的各种复杂状态、包括描述混沌神经元活动及其有规律的轨迹而提出的一个精致的嗅觉球状模型);(3)汤森(James Townsend)(1992)的动力振动理论模型(van Gelder,1995,p.357);此外,还有埃玛尔(Jeffrey L.Elmural)关于语言的动力学认知模型,吉特迪(Marco Gitorti)在《关于认知的几个动力学模型》中给出的关于意识的动力学模型的其他例示(van Gelder,1995)。
[②]瓦里拉在《涉身心智》中特别引入了“生成的”(enactive)概念说明这一过程。(F.J.Valela, 1991,pp.8-9.)
交互隐喻与涉身哲学 ——认知科学新进路的哲学
发布时间:
阅读量: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