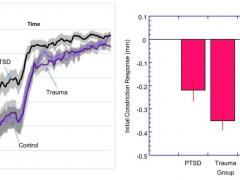在当代心理学与精神医学里,凯‧杰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1946-)可以说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她于1970年代在UCLA首创疾患特别门诊,很快地就成为国际知名的及忧郁症的专家。她在这些方面的专长与贡献,可以说在1990年出版将近千页的专著《躁郁症》时达到了颠峰。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本「经典之作」问世后五年,她勇敢地站出来,在她发表的第一本自传《躁郁之心》里坦承自己数十年来一直都是道地道地的躁郁症患者,长时挣扎于「疯狂」的边缘,也在鬼门关走过了好几回。此书一出,举世哗然。读者反应两极,支持、感谢的人固然占大多数,质疑、责难的声浪,亦复不少。有些专业人士担心她「败坏」精神医学的形象;保守人士攻击她不知廉耻,对自己的「败德丧形」津津乐道;狂热份子说她活该罹病,因为这证明了她信仰的不足。更有甚者,许多相信幽浮(UFO)及外星人的人(有这种想法的人,据估计光在美国就不只百万),纷纷来信「印证」她在躁狂期游历太空、直抵冥王星的经验,劝她「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作为一位执业多年的临床治疗师、资深教授、医学研究者,杰米森这一告白是有相当风险的。她的专业执照有可能被吊销,她的同事可能会质疑她的判断,她的学生也许不再信任她的教学,研究者或许会担心她过份主观(她可能因而不再申请得到研究经费)。身为霍普金斯大学的终生教授,她为何决定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这个心路历程在她的第二本自传《一切都已不再》里有相当详尽的描述。她最基本的动机,当然包括她对时时刻刻费尽心机隐藏病情病史的厌倦。同时,她也一直认为「言教」不如「身教」,期望经由「现身说法」,用自己亲身的体验来教育大众乃至专业人士,从而增进一般人对「躁郁症」的了解与接受,减少其被污名化的程度。但是最后真正促成她痛下决心,将她一生的病情巨细靡遗地公诸于世的,则是来自其时与她新婚不久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怀耶特(Richard Jed Wyatt;1939-2002)的不断督促与鼓励。怀耶特不幸于《躁郁之心》出版后没几年就疾病缠身,在2002年63岁时英年早逝。七年后杰米森在《一切都已不再》的书里对他们缠绵将近二十年的「跨世纪」恋情,以及怀耶特过世后她的哀悼与调适,都有十分生动感人的描述。细读此书,才真正了解,他们两人各自的人生,都是如此地艰难险阻,却也同时是如此地丰富多彩。
热情洋溢的代价
杰米森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她的父亲是专业的气象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空军军官。她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位长她三岁的哥哥及大她一岁的姊姊。就如许多其他职业军人的家庭,在三兄妹成长的过程里,他们随着父亲职位的调动而经常搬家转学,由华府、夏威夷到东京等等,需要不时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
营区生活,一方面固然给他们的童年带来较多的保护与安定感,但是同时自也有其枯燥无味的一面。幸而他们的父亲是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他笑口常开,「人未到声先到」,经常出人意表,怪点子层出不穷。但是有时候他忽然就安静下来,几个星期阴霾满面。不过他总是很快就拾回他的欢乐。与此相较,杰米森的母亲则是一位非常稳定、踏实、善体人意、不轻易波动的人。三兄妹中,大哥性情温和、进取、处世为人处处得体,后来成为知名的经济学教授。杰米森的姊姊,从小情绪就非常不稳定,很早就因严重忧郁而长期接受治疗,似乎一事无成。杰米森患病后得到的最主要的支持,则来自其大哥及同样「处变不惊」的母亲。
杰米森从小品学兼优,又得人缘,体育及其他课外活动也都出类拔萃。她从初中起就经常在营区军医院打转,问东问西,也收集种种生物标本,立志要习医并从事生物学研究。直至高二,她的生活似乎一直都无忧无虑,如鱼得水,自在自如。那一年杰米森的父亲自空军除役,在加州洛杉矶找到新的工作,全家搬到高级住宅区太平洋岬(Pacific Palisades)。之后不久,她父亲情绪起伏的状况却开始恶化。以前的「热情洋溢」,逐渐转变成自大狂妄、轻举妄动。以前持续几天到几星期的沮丧退缩,变成经年累月的自怨自责与激动不安,最后终至无法工作,被迫辞职。在这期间,他与杰米森母亲的关系也逐渐恶化,终于走向离婚。
杰米森自己对这「新天地」的适应,也是困难重重。她第一次发现,她不再是全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也不再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她没有想到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富可敌国」的人家,她许多同学生活的豪华奢侈,让她瞠目结舌。她从小在军营里养成的循规蹈矩的举止,被人当作笑话。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杰米森第一次陷入长期的严重忧郁。她对生活完全失去兴趣,她的世界也失去了色彩。她沉陷在绝望里,无法想象继续存在的理由,寻死的意念无所不在。靠着她从小的教养与习惯,她居然还能勉强掩饰这些症状,尽力去做她该做的事。但是这样子「行尸走肉」式的生活,自然是度日如年的。
每次这样愁云惨雾的日子一开始,到底会持续多久,她无从预测。但是她渐渐发现,每次忧郁期开始之前,她总有几天心情特别开朗, 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多年后回想起来,她才了解,那其实是她的「轻躁期」(hypomania),也是她陷入「忧郁期」之前的警讯。情绪的困扰,让她决定放弃习医的打算;家庭经济的拮据,导致她无法就读从小梦想要去的芝加哥大学,「将就」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在那里她遇上了两位对她另眼相待的心理学教授,由是决定了她一生的方向。
1974年27岁的杰米森得到博士学位,随即获聘为母校的助教授。那整个夏天她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才思敏捷,论文写作废寝忘食、日夜不休。宴会里她穿得花枝招展,在人群中往来穿梭,高谈阔论、喋喋不休。她有用不完的精力,经常与同事、朋友彻夜狂欢,在校园里、空旷的停车场上来回狂奔,差一点就被校警逮捕。枉费了她的博士学位,她对自己第一次进入真正的「躁期」浑然不觉。对杰米森来说,忧郁犹然可以勉强掩饰,到了躁期,她可就「原形毕露」了。不幸这躁与郁的循环,却愈来愈紧凑。更不幸的是,到后来她的躁期里又混入了「激动性忧郁」(agitated depression)。旺盛的精力加上彻底的绝望,自残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事了。
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那么杰米森的躁郁症为什么会反复发作呢?据她所说,这一大部分要归罪于她本人对药物治疗的抗拒。杰米森发病的时候,锂盐刚被引进美国,她亲身体验、亲眼见证其奇妙的功效。借着锂盐,杰米森可以预防躁期的来临,也可以减轻郁期的症状。但是伴随着锂盐,尤其是高剂量锂盐的,是许多恼人的副作用:胃肠不适、频尿口渴、肌肉颤抖、动作笨拙等等。长期服用锂盐还有可能影响甲状腺及肾脏的功能。更可怕的是,过量的锂盐会导致谵妄、昏睡、体温失调、甚至死亡。职此之故,定期血液检验必不可少。药物治疗的反应因人而异。锂盐对杰米森药效奇佳,但是副作用也特别明显。对副作用的抗拒,于是成为杰米森屡屡停药的借口。当然比此更重要的原由,还是在于她与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一样「讳疾忌医」,不愿意接受疾病随时会复发的可能及有长期治疗的需要。此外,就如多数躁郁症患者,杰米森也难免会不时怀念「轻躁期」及躁症初发时旺盛的精力、自信与特别愉快的心情。因而,她一次次停药,一次次旧病复发。躁症期冲动放浪、一掷千金、债台高筑,也导致工作停顿、破裂;郁期万念俱灰、「痛不欲生」。她从发病到真的有完全的「病识感」(接受自己有病在身,需要持续治疗)之间,延宕了一二十年。
杰米森与锂盐的「长期抗争」不免让人想起古书里常会读到的一句话:「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这句话常被用来劝谏在位者接受批评,因为「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它之所以会被如此引用,想必是因为它曾经是人尽皆知的道理吧!的确,无分中西古今,药就是毒,「运用之妙,在于调节因人而异的剂量」,十六世纪的欧洲医学大师Paracelsus(1493-1541)也就是这么说的(“The dose makes thepoison.”)。
劫后余生,分外灿烂
杰米森在1985年与怀耶特相识相恋时,两人都已「功成名就」,同时也可以说是「历尽沧桑」了。出生于1939年的怀耶特来自芝加哥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就有严重的阅读障碍(dyslexia),但是由于身为律师的继父的鼓励,他并没有气馁,而是每天多花几个小时去把功课作完。终其一生,他发表的八百多篇论文、出版的六本书里,一字一句,无不是念了又念、改了又改,否则一不留神,就会写出错别字。为了弥补他阅读方面的劣势,他常到各处的博物馆直接观察,由此培养出对生物学的兴趣,奠定日后习医的基础。
他在28岁完成精神科专业训练后不久进入美国国家心理卫生院设立在圣‧伊莉萨白医院(St.Elizabeth Hospital)的研究中心时,就开始推动生物精神医学的研究,应用各种先进科技来了解精神分裂症及其他脑神经系统的问题,可以说是领风气之先。数十年来,他训练了许多优秀的精神医学研究者,「桃李满天下」。但是就在他35岁似乎一帆风顺、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罹患何杰金氏恶性淋巴癌(Hodgkin'sdisease)。这种病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一种死刑的判决。但是怀耶特没有放弃,他找到了当时在这一方面最顶尖的权威,一起决定「死马当活马医」,使用非常高剂量的放射线治疗,居然得到完全的痊愈。
怀耶特的确捡回了一条命,他死里逃生,换来二十年的健康,但是最后还是免不了要付出代价。原来高剂量放射线治疗有其种种长期的后遗症,包括心肌梗塞及因辐射引发细胞突变而发生的种种癌症。怀耶特在与杰米森结婚之前一年,险因心肌梗塞致死,幸而抢救得宜,完全康复。两人结婚四年,经过一阵子的磨合期,感情益深,生活日愈顺遂美满的时候,怀耶特的身体忽然开始急速衰弱,断层扫描发现肝肺、直肠都已有肿瘤——这次是非何杰金氏的恶性淋巴癌(Burkitt's lymphoma)。此时肿瘤医学已有重大突破。种种创新的抗癌药物「火力全开」,终于清除了所有的肿瘤,同时也把怀耶特整得「七荤八素」、「死去活来」。须发皆落自是不在话下,日以继夜的呕吐更是难熬。最严重的时候,他觉得整条肠子就如蛇在脱皮一般,掉得干干净净。当然在这过程中,他全身所有的白血球也都已「壮烈牺牲」了。所幸此时自体干细胞移植的技术也已趋成熟,先前抽取储备的干细胞又被移植回他的骨髓里,重新开始制造新的白血球。可惜他们的欢乐,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半年后怀耶特肺部又出现肿块,这一次的癌症来势凶猛,「正规」治疗方法已无效验,尚在试验中的治疗方法,成效亦属有限。然而拜科学发展之赐,怀耶特毕竟又多活了一年,让他的同僚有时间筹备盛会,感谢他一生的贡献,也让他有时间能与杰米森共享诸如清晨到公园观赏百年难得一见的流星雨的时光。
杰米森在《一切都已不在》的前半部里叙述的重点,放在怀耶特生病之后,尤其是到最后怀耶特罹患末期肺癌,无药可治之时,他们经历的心路历程。她对他们相识及婚姻初期因她的躁郁症及两人性格的差距所带来的问题轻轻带过。但是字里行间读者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试探与摸索中,一步步开展出来的。杰米森结识怀耶特之前独居多年,已发展出一套对付情绪起伏乃至躁郁症发作时的因应之道。身边多了一个人,生活跟着复杂起来。虽然怀耶特是一位精神科医师,对躁郁症应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他有可能跟一个随时会发作的病人住在一起吗?杰米森一次次的问,怀耶特一次次地说:「我爱的是整个的妳,包括妳的躁郁症。我既然要与妳在一起,也就打算与妳的躁郁症共存」。这话说来容易,可贵的是他真的做到了。往后的日子里,打打闹闹自然还是难免,但是怀耶特的内敛自制,以及他看似单纯的讯息(「定时吃药、充分、我就在妳身旁」),给杰米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然而杰米森给怀耶特带来什么呢?怀耶特说「他倚靠她,她给他带来心灵的安宁。」杰米森百思不解,她不是一向都有如风暴,怎么会给人宁静呢?或许是怀耶特一向压抑的情绪,因与她在一起而得以表达、发泄,从而得以平静吧!杰米森后来这么想。
他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年,怀耶特缠绵病榻,杰米森打点一切,忙前忙后,似乎连躁郁症都被挤在一旁。病情好转时,他们一起感受喜悦,但是随着怀耶特症状的复发与恶化,他们也不时面对病痛的折磨及大限将临的恐惧与绝望。既奇异又可贵的是,现实世界里这么沉重的打击,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起伏,却似乎没有导致杰米森躁郁症的发作。他们几乎到了最后一刻,都还没有完全放弃奇迹出现的可能,但是也对怀耶特的身后事早有准备。怀耶特的预立遗嘱简单明确;他们最后的别离,也就免除了许多无谓的迟疑与挣扎。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一切都已不再》的后半部生动描述杰米森在怀耶特过世后如何渡过她的哀悼期,如何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她最强调的是,哀悼无论如何的痛苦,与忧郁症的症状是全然有别的。丧亲的哀痛既深且巨,但并非无边无际。哀悼一阵一阵来袭,而哀悼的人好似少了一层皮,裸露于这大千世界里,一切都是太强的刺激,哀悼者因此需要独处的空间与时间。与此相反,忧郁的人感觉为世界所弃绝,离群索居只有益增其痛苦与自杀的危险。哀悼者为失去与所爱之人共享的生命而哀伤,忧郁的人则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哀悼者对未来保有「可能」的希望,忧郁的人则濒临绝望。与此同时,哀悼是为社会所认可的人生过程,哀悼的人常能由社会认可、提供的礼俗仪式得到慰藉;忧郁的人则常自绝于世,也为社会所不容。
除此之外,杰米森也认为她半生与躁郁症纠缠的「历练」,对她之所以终能走出哀悼,是颇有帮助的。因为生了那么多年的病,她从来就理解,人的情绪是变动不居、无可掌控的。哀悼诚然痛彻心腑,但是比起濒临疯狂或死亡的躁郁症,就不见得是那么地不能承受了。她既然能通过躁郁症的考验,就应该也能走过哀悼的幽谷吧!
冬去春来,杰米森的哀伤,果然就逐渐淡化。是什么因素抚平了她一部分的伤痕?亲友的支持?音乐诗词的安慰?欢乐时光的?还是时间本身的帮助?杰米森觉得她的确是个幸运的人,因为她拥有这么多帮助她脱离困境的条件。她的复原,让她得以完成她在怀耶特尚在人间时开始撰写的《热情洋溢》这本书,以及其后出版的《一切都已不再》,从而让我们对躁郁症及丧偶哀悼的心路历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此而言,她的复原,也实在是我们许多人的福气。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