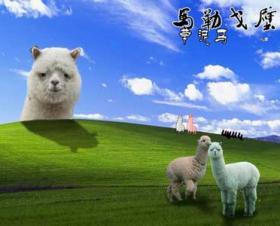认知发展、隐喻映射与词义范畴的延伸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形成的认知机制
彭宣维[①]
(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汉民族集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和隐喻映射手段,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以词串和词族为代表——形成的内在历时机制。这里将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议题:(一)认知过程和新范畴形成的相互关系;(二)隐喻映射在词义范畴扩展和词义网络体系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映射的主要类别;(三)源范畴和目标范畴通过能指成分形成词义范畴网络体系的内在机制。从而说明以词串和词族为标志的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历时语用过程。
关键词:认知;词义范畴;词汇;源范畴;目标范畴;隐喻映射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 (2004) 03-
一 引言
首先是本文的基本对象、目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从研究对象和目的看,本文试图以词串和词族的语义范畴为着眼点,考察汉语词义范畴(Lexical semantic category)的扩展和延伸过程,从而说明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形成的历时机制。理论依据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1]、发展语言学(尤其是语言的历时—共时整合观)[2]以及其他相关理论(如索绪尔的符号观)[3]。研究方法是自下而上的,即从词串和词族现象入手,上升到对词义范畴的形成与认知深化的关系的探讨,最后落到起支配作用的隐喻映射手段上。结论是,汉民族集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和隐喻映射手段,在汉语词义范畴的扩展和延伸以及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形成的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相关研究背景和相关议题。语义范畴的扩展问题,此前台湾学者曹逢甫等已从“身体”以及身体器官的角度,对汉语相关现象进行了论述[4]。但我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词串”和“词族”现象,还缺乏更明确的了解,尤其是词义范畴以及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形成的内在机制。为此,本文拟从词义范畴的延伸和认知发展的互动关系,来揭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演进历程。
三是相关概念和术语的使用,包括词串、词族、隐喻映射以及标题中使用“延伸”一词的原因。(一)词串(Word chain)是指汉语中以同一个语素为基础形成的词项关系。例如,血气,血腥,血液;脓血症,抗血清,干血浆;贫血,心血,浴血。“血”这一语素分别出现在词首、词中和词末,从而形成由同一语素构成的词串。(二)“词族”(Word family)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特征的一组词所形成的词项系统[5],如“拥挤”、“摩肩接踵”和“水泄不通”,或者“安静”、“宁静”和“沉寂”等。因此,这里不讨论具有相同经验语义特征的词串,因为这一类词串在很大程度上与词的(褒贬评价和正式性)人际意义有关,拟另议。可见,词族可以是词串,如安静和宁静;但词串不一定是词族。
(三)词义扩展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是以“经验基础”(Empirical basis)为前提的认知“推理”(Reason),这是隐喻映射的工作机制。认知语言学家莱可夫和约翰逊[6](PP.3~4) 在提出“经验”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这一与西方传统认识论相悖的基本观点时指出:“推理不仅包括我们进行逻辑推断的能力,也包括我们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做出评价、提出批评、审视我们该如何行动、理解我们自身、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能力。”而基于经验基础和推理的隐喻(Metaphor)和隐喻映射(Metaphorical mapping),则指以相似性(Resemblance)为推理依据、通过一种概念诠释另一概念[7](P.105)的认知过程:
隐喻不仅是根据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模式来认识和构造对其他事物的认知模式,而且是将整个认知模式的结构、内部关系转移,这种转移被称为源模式向目标模式结构的映射(mapping of the structure of a source model onto a garget model)。这种映射是经验和理解的结果。
(四)标题中有一个与词义范畴有关的“延伸”概念。我们在行文中还将根据情况把“扩展”和“拓展”作为替代性近义成分使用。标题中使用“延伸”一词,指在以词串和词族为着眼点的汉语词汇系统中,各相关词义范畴之间不是离散关系,而是以一些基本范畴为中心延伸开去的词义特征束和范畴家族,彼此之间有含盖和交叉关系,从而形成各种系统关系;当然,使用“延伸”而不是“扩展”,还有对标题的音韵关系的考虑。
最后是本文的组织。作者拟首先说明认知能力的深化与词义范畴扩展的关系,然后说明隐喻映射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相关作用,最后阐述隐喻这一现象在新范畴的形成以及认知深化过程中发挥的直接作用,由此揭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复杂纷繁的历时原因。
二 认知能力和词义范畴的同步拓展
这里拟具体讨论认知能力深化与词义范畴拓展的关系。先看几组彼此平行的语义范畴。
(1)a. 城楼,钟楼,宫殿,教堂,牲口棚,厂房,宿舍;b. 别墅,公馆,摩天大楼;c. 山门,车门,防盗门;d. 更衣室,卫生间;e. 画室,灵堂,病房,舞厅,机房
这里列出了五组成分,各组内成分之间彼此平行,没有交叉涵盖关系。由于人类生活和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面临的事物增多,认知能力得到了深化,语义范畴增多了,各类成分也随之增加。这是从范围上彼此同步拓展的实例。
还有从深度上同步扩展的大量实例。以“车”为例。先看《汉语大字典》[8](P.1462)有关“车”的引文。
《說文》:“車,輿輪之總名,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輚,籀文車。”段玉裁注:“謂象兩輪、一軸、一輿之形。此篆橫視之乃得。”“(籀文)从戈者,車所建之兵莫先于戈也。從重車者,象兵車連綴也,重車則重戈矣。”
《说文》从造型方面说明了该字的来源,段玉裁则从“车”的形状和功用上加以阐述。由此可见“车”在上古汉语里的形状及其主要功用:包括车轮的形状以及车厢的外观,而其主要功用是用来打仗的。但随着人类的进步和近代科技的发展,“车”的类型和功能增多了,因此其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形成大量新概念和新的表达成分,这在现代汉语中尤为突出。首先,下面是有关范畴的一些常见的功能性成分:
(2)班车,保温车,殡车,兵车,餐车,叉车,铲车,铲运车,吊车,粪车,货车,加油车,交通车,绞车,教练车,柩车,救护车,救火车,救陷车,救援车,客车,矿车,垃圾车,冷藏车,灵车,旅行车,跑车,起重车,牵引车,寝车,囚车,区间车,洒水车,赛车,扇车,拖车,卧车,消防车,行李车,宣传车,压裂车,游览车,战车,直达车,指挥车,专车,军车,越野车
其次是从外观或构成上对“车”的分类:
(3)彩车,敞车,大板车,平板车,棚车,篷车,敞篷车,架子车,花车,罐车,大车,小车,斗车,列车,独轮车,三轮车
三是从速度上的分类:
(4)特快车,快车,慢车
四是从动力来源方面的分类:
(5)机动车,电车,(附)挂车,火车,机车,电机车,内燃机车,马车,牛车,电瓶车,汽车,手车,手推车,人力车,兽力车,自行车
还有其他多种类别,其中好些是混合型的,例如:
(6)功能+外观:“翻斗车”
功能+外观+动力来源:“轿车”,“大轿车”,“小轿车”
动力+功能:“耧车”
外观+感觉:“闷子车”,“闷罐车”
归属:“校车”,“厂车”,“公车”,“私车”
材料:“铁甲车”,“装甲车”
时间:“早车”,“首车”,“晚车”,“末车”,“夜车”
空间:“天车”
时间+空间:“加车”
构成与设备:“软席车”,“硬席车”
使用对象:“男车”,“女车”
来源:“洋车”
翻译:卡车,摩托车,吉普车
还有不便分类的“缆车”。但作为每一个成分的语义范畴而言,它们都是在基本范畴(Basic category)“车”的基础上形成的“下位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y)。还有与“车”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风车”,“水车”,“纺车”,“指南车”,“舟车”,这是隐喻映射的结果:前四者可能是因为它们均有轮子状的装置,这些装置均可以转动;而“舟车”是“舟”和“车”合二为一的复合词,借用来指“旅途”,属于借喻性映射[1]。
据此,我们便可了解相关词义特征和范畴的拓展是如何对人类的认知能力的提高发挥作用的,也可反过来观察认知能力的提高对词义范畴和新词项的拓展产生影响的。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一)以上好些词的语义范畴之间具有涵盖或交叉关系,如按时间早晚划分的类别与一部分按动力或功能划分的“车”。它们一方面与基本范畴“车”之间形成上下位关系;另一方面,它们自身则主要构成相互平行或彼此交叉的、具有同等地位(即都是下位范畴)的关系。(二)通过词义范畴的确定,可以观察大脑处理经验知识的方式。(三)认知能力和词义范畴同步扩展的结果是,人类的整体认知能力增强了,汉语的词汇系统也随之得到了丰富。这一点尤可通过近义词之间的差别来说明。以“灵车”和“柩车”两个成分所体现的概念为例。两者具有相同的所指范畴,但彼此的词义范畴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自的辅助性语素“灵”和“柩”:“灵车”侧重于“运送灵柩或骨灰盒”这一功能,而“柩车”主要指“装着尸体的棺材”的车。正是彼此的这种分别,才使人们的经验知识得到了更具体的界定。(四)词的语义范畴并非独立于认知能力本身,而是受后者支配的,因为我们有认识上的分别才会有不同的词义化方式,所以,认知过程为词义特征的生成提供了基础,为不同的“语义空间”(Semantic space)——即语义范围的进一步细分、并通过词项体现或表征出来[9](P.289)——提供资源,从而形成复杂的词义网络;通过映射,同一语素既可以诱发新的经验范畴的形成,还能提供更为明确的界定框架。
再来看下面几组有关“死亡”的词。
(7)a. 崩,驾崩,山陵崩,晏驾,升遐,登遐,宾天,大行,千秋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