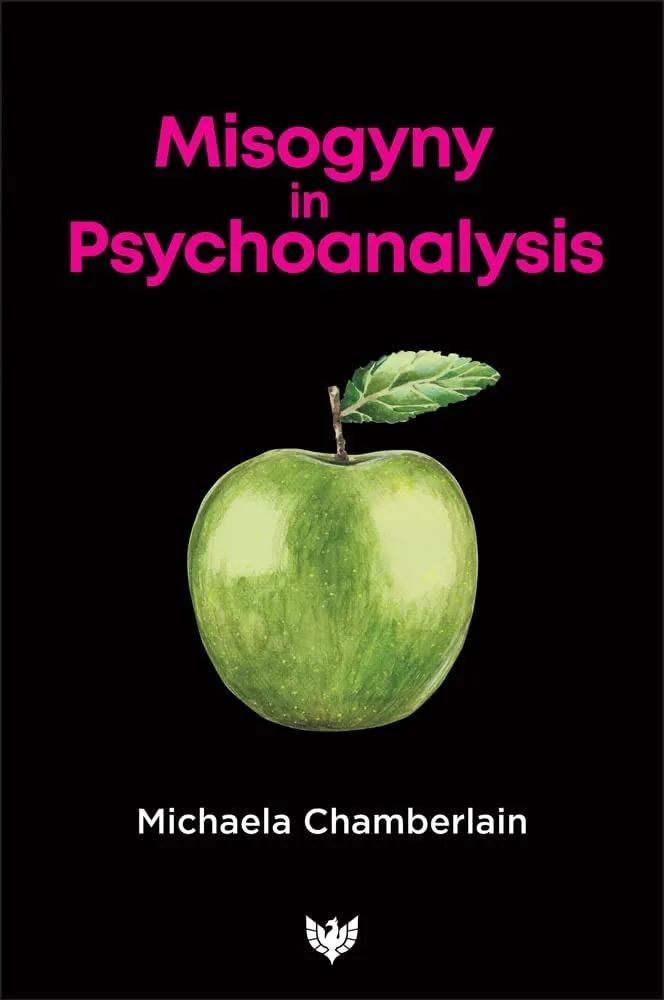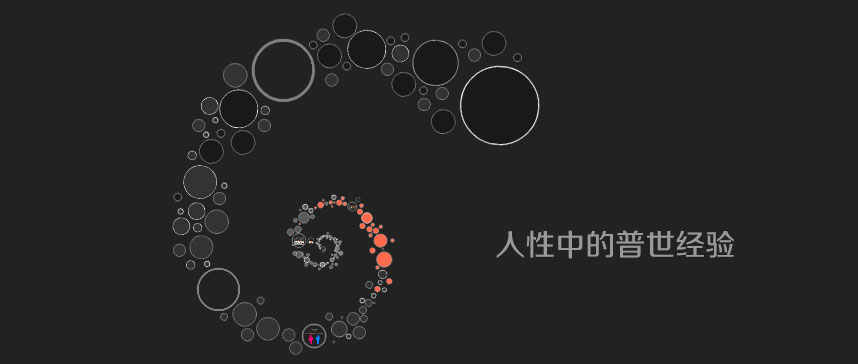对农村的影响机制:追踪研究 *
范兴华, 方晓义,, 黄月胜, 陈锋菊, 余思
心理学报, 2018, 50(9): 1029-1040
doi: 10.3724/SP.J.1041.2018.01029
摘要
为考察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的影响机制, 采用父母关爱问卷、、问卷、问卷和抑郁量表对279名四年级和七年级农村儿童进行2.5年追踪调查。以前、后测间一直处于相同留守状态的207名儿童为分析对象, 结果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前后测中单、双留守儿童报告的父母关爱均较少、抑郁均较高; 双留守儿童的后测抑郁显著高于前测; 控制性别对抑郁的作用后,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有即时与延时负向预测效应; 即时预测中, 自尊、神经质起部分中介作用; 延时预测中, 后测自尊、神经质起部分中介作用; 增加控制后测父母关爱对后测抑郁、自尊、神经质的作用后, 前测父母关爱对后测抑郁的直接效应降低但仍接近显著, 同时对后测自尊、神经质的直接作用不显著; 上述两种控制条件下, 前测父母关爱与前测友谊质量交互项对后测自尊与神经质的预测作用均显著, 随着友谊质量的提高, 父母关爱对自尊、神经质的延时影响增大, 后测自尊与神经质的中介效应随之增强; 该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
关键词: 留守儿童 ; 父母关爱 ; 抑郁 ; 自尊 ; 神经质人格 ; 友谊质量
1 问题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基于经济原因, 许多农民工将未成年子女留在家乡, 由父母一方监护或祖辈、亲戚代管。这些未成年人被称为“农村留守儿童”, 简称留守儿童。据全国妇联课题组推算, 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约为6102.55万, 且人数呈逐年增长之势。由于亲子分离常给未成年子女带来问题, 因此,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引起了社会关注。
抑郁是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 是一种感到无力应对外界压力而产生的消极情绪。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的抑郁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侯珂, 刘艳, 屈智勇, 蒋索, 2014; Liu, Li, Chen, & Qu, 2015)。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diathesis-stress theory) (Monroe & Simons, 1991)认为, 抑郁发生受到压力和素质的共同影响。其中, 压力泛指重大生活事件、生活中的不利变化等; 素质指易患抑郁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一方面, 压力激发了素质, 素质使得患病的潜在倾向变为现实, 即压力通过素质的中介影响抑郁发生; 另一方面, 素质调节着压力对抑郁的影响程度, 随着素质水平提高, 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增大。而且, 压力会引发个体对支持资源的需求, 低社会支持将增加个体的抑郁易感性(Auerbach, Bigda-Peyton, Eberhart, Webb, & Ho, 2011), 积极的友谊关系则有助于个体的压力适应(Zhao, Liu, & Wang, 2015)。就留守儿童而言, 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父母关爱, 许多儿童因此变得敏感和自卑, 不仅在意别人看法, 也对自己失去信心, 并伴随有委屈、无助、忧虑等抑郁体验; 为缓解关爱缺失带来的不利, 他们会找朋友玩耍、谈心等(周宗奎, 孙晓军, 刘亚, 周东明, 2005; 范兴华, 2012)。上述现象中, 父母关爱缺失(压力)与抑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 以敏感、自卑为主要特点的神经质人格、低自尊在此关系中是否扮演了素质的角色?所起作用是中介是调节抑或两者兼有?同时, 以谈心等活动为内容的同伴友谊能否有效缓解相应不利?素质压力理论为此探究提供了理论框架。
1.1 父母关爱缺失与留守儿童抑郁情绪
Hobfoll (2001)认为, 压力是个体与环境间的平衡状态被破坏后, 个体资源遭到损失或损失的威胁或不能获得充足资源产生的, 此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人际关系资源。父/母外出后, 亲子缺少直接互动, 留守儿童的父母关爱资源面临缺失。父母关爱(parental care)是父母教养行为的重要方面, 在西方指父母在心理和层面对孩子的关注和接纳(Lancaster, Rollinson, & Hill, 2007); 在我国可分为情感关爱与物质关爱, 其中, 前者与西方概念一致, 后者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王燕, 张雷, 2007)。留守情境下, 父/母给予孩子的物质关爱少, 但一般会通过电话等媒介与孩子交流, 关注和指导孩子成长。鉴此, 范兴华(2012)将“父母给予儿童帮助、指导、鼓励、肯定以及与孩子沟通交流等发生的情况”定义为父母关爱, 强调对孩子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关注和接纳。研究发现,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留守儿童感知到的父母关爱少(范兴华, 2012), 对家庭领域的需要更未得到满足、被父母所爱的需要更加强烈(常青, 夏绪仁, 2008)。按照Hobfoll (2001)的观点, 父母关爱资源被减损或需求未被满足, 将给儿童带来压力感。
研究发现, 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Quach, Epstein, Riley, Falconier, & Fang, 2015)和父母支持(田录梅, 陈光辉, 王姝琼, 刘海娇, 张文新, 2012)对抑郁有负向预测性, 童年期的父母关爱对成年期抑郁有显著预测作用(Lancaster et al., 2007)。说明, 父母关爱缺失是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 对抑郁有即时和延时影响。这种建立在亲子直接互动基础上的关爱效应是否适用于与父母长期分离的留守儿童?我们认为, 尽管关爱形式发生了变化, 但本质并未改变。据此假设H1: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有即时与延时负向预测性。
1.2 自尊、神经质人格对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关系的中介与调节
自尊是个体对的情感性评价, 影响其对周围环境的应对:高自尊者倾向于对环境信息进行积极加工, 更多表现为乐观、自信和成功期望; 低自尊者对环境中的负性信息存在注意偏向, 更多体验到抑郁等消极情绪(Sowislo & Orth, 2013)。神经质是与负性情绪体验有关的人格因子, 表现为情绪稳定性的差异:高神经质者易情绪化, 自我图式较消极, 有保持负性信息的倾向, 遭受打击时容易产生沮丧等消极情绪; 低神经质者多表现为平静, 较少出现不良情绪反应。Roberts和Kendler (1999)发现, 自尊和神经质一起对抑郁进行预测时, 主效应均显著, 表明两者是结构上既关联又独立的抑郁素质。不仅如此, 它们亦可作为社会性发展结果的指标。自尊反映了个体对自我的理解, 是一个波动的动态结构, 容易受到各种内外压力的影响(Ramsawh, Ancoli-Israel, Sullivan, Hitchcock, & Stein, 2011)。神经质是人格的核心成分之一, 出现在童年晚期, 随年龄增长稳定性增加, 成熟于成年期; 在此期间, 童年逆境、慢性生活压力对其发展有消极影响(Ramsawh et al., 2011; Uliaszek et al., 2010)。研究显示, 自尊部分中介了父母关爱对大学生感(曾晓强, 2010)和童年期父母关爱对老年期压力反应(Engert et al., 2010) 的影响; 神经质部分中介了慢性生活压力对青少年抑郁(Uliaszek et al., 2010)和童年逆境对大学生质量 (Ramsawh et al., 2011)的影响。总之, 压力通过自尊与神经质的即时与延时中介对健康产生影响。
低自尊或高神经质者的抑郁易感性较高, 可能导致压力对抑郁的影响加重。自尊的缓冲假说认为(Orth, Robins, & Meier, 2009), 压力情境下, 低自尊者因缺少足够的应对资源而容易遭受抑郁, 高自尊者因拥有较多的应对资源能有效缓解压力带来的不利。阳性乘法模型(the positive multiplicative model)指出, 神经质与逆境对疾病风险存在交互影响, 神经质水平越高, 逆境对疾病风险的影响越大(Kendler, Kuhn, & Prescott, 2004)。研究发现, 自尊能缓解总的生活压力对大学生抑郁(Eisenbarth, 2012)、低水平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抑郁(党清秀, 李英, 张宝山, 2016)的影响, 但不能减弱压力事件数目(Orth et al., 2009)、不同领域的生活压力(Moksnes, Eilertsen, & Lazarewicz, 2016)对青少年抑郁的消极效应; 神经质会加重累积压力对普通成人抑郁症(Vinkers et al., 2014)和慢性压力对病人抑郁症初始水平及其变化(Brown & Rosellini, 2011)的不利影响, 但不能调节生活压力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的作用(Yang, Chiu, Soong, & Chen, 2008)。这说明, 低自尊和高神经质只会加重某些特定压力对抑郁的 影响。
日常生活中, 留守儿童需面对父母关爱缺失压力; 同时,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 其自尊较低, 神经质与抑郁水平均较高(Liu et al., 2015; 兰燕灵等, 2009)。这是因为父母关爱缺失抑制了自尊与神经质人格的发展从而导致抑郁上升?抑或因为自尊降低与神经质提高, 引发儿童对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增加, 进而加重了父母关爱缺失对抑郁的影响?基于前述论证, 我们推断, 这两种影响途径可能同时存在。故假设如下:
H2: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预测中, 自尊与神经质既起中介作用又起调节作用。调节作用中, 自尊有加强效应, 神经质有减弱效应。
H3:在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延时预测中, 后测自尊与神经质既有中介效应又有调节效应。
1.3 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缺失与抑郁、自尊、神经质关系的调节
作为重要的支持资源, 同伴友谊可使儿童学会情绪表达与调节、获得情感支持和体验到与信心(Wen & Lin, 2012), 也具有潜在治疗功能, 能帮助逆境中的儿童健康成长(Zhao et al., 2015)。研究发现, 同伴关系越好, 亲子疏离感对青少年抑郁(Jager, Yuen, Putnick, Hendricks, & Bornstein, 2015)和父亲过分干涉对犯罪青少年神经质人格(彭运石, 王玉龙, 龚玲, 彭磊, 2013)的影响越小; 同伴接纳度越高, 低父子对儿童自尊的影响越弱(Pinto, Veríssimo, Gatinho, Santos, & Vaughn, 2015)。可见, 同伴关系能调节亲子关系变量对儿童抑郁、自尊、神经质人格的影响。父母关爱隶属于亲子关系, 同伴友谊是同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亲子长期分离, 留守儿童将会更多地与同伴交往, 友谊对亲子关系与人格发展关系的影响可能更大。据此假设H4:友谊质量能增强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自尊、神经质人格的即时影响。
其次, 积极的同伴交往经验能培养儿童的角色采择技能, 有助于儿童理解他人的思想与情感; 童年期的父母关爱对成年期抑郁(Lancaster et al., 2007)、自尊(Engert et al., 2010)、神经质人格(Reti et al., 2002)均有延时预测效应。由此推断, 同伴友谊能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父/母外出打工的动机, 进而缓解父母关爱缺失对人格发展的长期影响, 故假设H5:友谊质量能加强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自尊、神经质人格、抑郁的延时影响。
再者,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对友谊质量的认识由对友谊外在行为特征的认识逐步深化为对内在的、情感性特征的认识, 转折的关键年龄为10~15岁。Sullivan指出, 友谊(尤其是之前建立的)能帮助青少年消除童年期的不良亲子交往经历给发展带来的不利。这意味着, 初中儿童对友谊质量的认识比小学儿童更深刻, 有助于他们消解父母关爱缺失压力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据此假设H6: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仅发生在初中留守儿童中。
进入青春期后, 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男性(Moksnes et al., 2016), 故分析时控制性别对抑郁的影响。综合各假设, 将其整合为图1即时预测模型(M1)和图2延时预测模型(M2)。由于父母对青少年早期子女的教养方式有较高稳定性(Moilanen, Rasmussen, & Padilla-Walker, 2015), 故M2在控制性别作用后增加控制T2父母关爱的作用, 以考察两种控制条件下T1父母关爱对T2抑郁的影响机制及其变化。对M1与M2检验时, 若T1友谊质量的调节效应显著, 则再考察它是否受学段调节。
图1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即时影响模型(M1)
图2 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抑郁的延时影响模型(M2)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根据父母外出情况, 可将留守儿童分为父亲外出、双亲外出和母亲外出三类儿童, 其中前两类占绝大多数, 且两者的抑郁得分差异是否显著尚无定论(侯珂等, 2014; Zhao et al., 2015)。借鉴以往研究范式, 以非留守儿童为对照组, 以父亲外出儿童、双亲外出儿童为实验组开展追踪研究。2009年10月, 从湖南省湘乡市2个乡镇选取3所初中与3所小学作为取样学校, 以班为单位对四年级、七年级学生进行前测(T1), 获得来自完整家庭的父亲外出且由母亲监护的儿童(简称单留守)116名、双亲外出且由祖辈监护的儿童(简称双留守)84名和父母从未外出且由父母监护的儿童(简称非留守)79名, 共279名。2012年5月进行追踪调查(T2), 获得有效被试264名, 其中57名被试监护类型和/或留守类型在追踪期间发生了改变而不参与分析。以前后测中一直处于相同留守状态的207名儿童为分析对象, 其中双留守72人、单留守79人、非留守56人; 男生110名, 女生97名; 四年级85人, 七年级122人。前测时被试年龄在8~14岁之间, 平均10.90 ± 1.58岁。
2.2 研究工具
父母关爱问卷 由范兴华、方晓义和陈锋菊(2011)根据Takahashi和Sakamoto编制的情感关系量表(ARS)修订而成, 共8题, 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年内父母给予其帮助、鼓励、指导等情况发生的频率, 5点计分, 1为很少, 5为非常多。计算项目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感知到的父母关爱越多。前后测中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86、0.89。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量表中文版(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共10题, 4点计分, 从1“非常符合”到4“很不符合”。将肯定表述题答案反向计分后求各题均分, 分数越高代表自尊越高。前后测中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79、0.83。
神经质人格问卷 选自邹泓(2003)修订的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 含9题, 5点计分, 1为“完全不像我”, 5为“非常像我”。计算项目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情绪稳定性越差。前后测中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73、0.81。
友谊质量量表 选自Gauze, Bukowski, Aquan- Assee和Sippola (1996)修订的青少年友谊质量量表(FQS), 共19题, 要求被试从伙伴关系、帮助与支持、安全性和亲密性四方面评价与最要好同性朋友的关系质量。5点计分, 1为“完全不符合”, 5为“完全符合”。计算项目均分, 得分越高代表友谊质量越好。前后测中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82、0.79。
抑郁量表 选自Radloff编制的CES-D中文版(汪向东等, 1999)。要求被试回答过去一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4点评分, 1为“偶尔或无”, 4为“大部分时间或持续”, 共20题。肯定表述题计分经反向转换后, 计算项目均分, 分数越高代表抑郁心情越严重。前后测中问卷Cronbach α系数为0.83、0.89。
2.3 数据收集过程
以班为单位施测。前测和后测中, 各校施测时间间隔均控制在1周内。施测时, 主试将题目逐个读给小学生听, 以助其理解后作答; 初中生被试在主试讲解指导语后独立作答。作答结束后, 主试检查问卷, 发现有漏答或乱答现象, 及时请被试补答或纠正或作废卷处理。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M1和M2模型包含的研究变量分别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M1 (χ2/df = 4.04, NFI = 0.85, IFI = 0.82, RMSEA = 0.142)和M2 (χ2/df = 4.54, NFI = 0.85, IFI = 0.77, RMSEA = 0.154)的单因子结构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均较差。说明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5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6.0与AMOS 22.0进行数据分析, 含初步分析与模型检验。初步分析包括MANOVA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模型检验含即时预测模型(M1)与延时预测模型(M2)检验, 且均分两步:(1)检验自尊与神经质在关爱→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对父母关爱→抑郁/自尊/神经质路径的调节作用; (2)检验自尊、神经质对关爱→抑郁路径的调节作用。其中, M2检验又分为仅控制性别作用和同时控制性别与T2父母关爱的作用两种情况。
3 结果与分析
3.1 初步分析
3.1.1 三类儿童的变量得分比较及其发展趋势
首先, 以儿童类型为分组变量, 分别以T1变量、T2变量为结果变量进行MANOVA分析。结果显示, 儿童类型的主效应在T1变量(Wilks, l = 0.85, F = 3.27, p < 0.001, η2 = 0.076)、T2变量(Wilks, l = 0.83, F = 3.95, p < 0.001, η2 = 0.090)中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 儿童类型在T1/T2父母关爱、T1/T2抑郁上的得分差异显著(见表1), 单、双留守的T1/T2父母关爱显著低于非留守(ps < 0.01), T1/T2抑郁显著高于非留守(ps < 0.05)。其次, 以儿童类型为被试间变量, 以测量时间为被试内变量, 进行3×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仅抑郁的测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F(1, 204) = 9.68, p < 0.01, η2 = 0.045), 双留守的T2抑郁显著高于T1抑郁(p < 0.01); 所有变量的测量时间与儿童类型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表1 三类儿童在变量上的得分(M ± SD)
| 变量 | T1 | F(2, 204) | T2 | F(2, 204) | ||||
|---|---|---|---|---|---|---|---|---|
| 双留守 (n= 72) | 单留守 (n= 79) | 非留守 (n= 56) | 双留守 (n= 72) | 单留守 (n= 79) | 非留守 (n= 56) | |||
| 父母关爱 | 3.22 ± 0.84 | 3.41 ± 0.85 | 3.89 ± 0.69 | 11.25*** | 3.18 ± 0.96 | 3.36 ± 0.86 | 3.76 ± 0.84 | 6.85*** |
| 自尊 | 2.81 ± 0.43 | 2.83 ± 0.47 | 2.93 ± 0.49 | 1.14 | 2.77 ± 0.41 | 2.81 ± 0.42 | 2.91 ± 0.44 | 1.66 |
| 神经质 | 2.98 ± 0.68 | 2.79 ± 0.82 | 2.76 ± 0.65 | 1.88 | 3.01 ± 0.66 | 2.83 ± 0.73 | 2.78 ± 0.72 | 2.02 |
| 友谊质量 | 3.77 ± 0.78 | 3.71 ± 0.78 | 3.76 ± 0.71 | 0.13 | 3.80 ± 0.62 | 3.88 ± 0.66 | 3.69 ± 0.84 | 1.24 |
| 抑郁 | 1.98 ± 0.46 | 1.92 ± 0.42 | 1.72 ± 0.32 | 7.10*** | 2.15 ± 0.45 | 2.01 ± 0.48 | 1.76 ± 0.44 | 11.69*** |
3.1.2 留守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非留守儿童作为对照组, 不再参与后续分析。对单留守、双留守、四年级、七年级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分别进行分析。Z检验显示, 单留守与双留守、四年级与七年级在变量的即时相关和延时相关系数上的差异均不显著。因此, 将不同留守类型、学段的留守儿童数据合在一起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 从同时性角度看, T1前测/T2后测中, 父母关爱与友谊质量(r = 0.23/0.25)、自尊(r = 0.38/0.34)、神经质(r = -0.37/-0.34)、抑郁(r = -0.42/-0.58), 自尊与神经质(r = -0.24/-0.32)、抑郁(r = -0.29/-0.47)以及神经质与抑郁(r = 0.33/0.37)的相关均显著(ps < 0.01); 友谊质量与自尊(r = 0.21/0.18)、神经质(r = -0.24/-0.32)、抑郁(r = -0.37/-0.31)的相关亦显著(ps < 0.05)。从延时性角度看, T1父母关爱与T2父母关爱(r = 0.61), T1父母关爱/T1友谊质量与T2自尊(r = 0.29/0.25)、T2神经质(r = -0.28/-0.18)、T2抑郁(r = -0.45/-0.26)的相关显著(ps < 0.05)。此外, T1/T2抑郁与性别(男 = 0, 女 = 1)的相关显著(r = 0.26/0.18, ps < 0.05), 与留守时间、学段(小学 = 0, 初中 = 1)的相关不显著, 故模型检验中仅控制性别的作用。
3.2 模型检验
3.2.1 即时预测模型M1的检验
首先, 对自尊与神经质的中介作用以及友谊质量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指数较差(χ2/df = 5.74, NFI = 0.81, CFI = 0.83, RMSEA = 0.178)。删除不显著路径(T1父母关爱×T1友谊质量→T1抑郁/自尊/神经质, T1友谊质量→T1自尊/神经质), 模型整体拟合指数良好(χ2/df = 1.47, NFI = 0.95, CFI = 0.98, RMSEA = 0.056); 同时, T1父母关爱→T1抑郁/自尊/神经质以及T1自尊→T1抑郁、T1神经质→T1抑郁的路径均显著(见图3)。从预测效应看, T1父母关爱对T1抑郁的总效应为-0.38, 其中直接效应-0.27, 占总效应的71%; 间接效应-0.11, 由T1自尊(-0.16×0.33 = -0.05)和T1神经质(-0.34×0.18 = -0.06)的中介效应构成, 占总效应的29%。Bootstrap检验发现, T1自尊、T1神经质的中介效应95%CI为(-0.10, -0.001)、(-0.12, -0.002), 均未包括0, 中介效应显著。说明父母关爱部分通过提升儿童自尊与情绪稳定性来减少抑郁发生。
上一篇: 自我意识及其研究概述 - 内蒙古心理网
下一篇: 提升记忆的小贴士 - 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