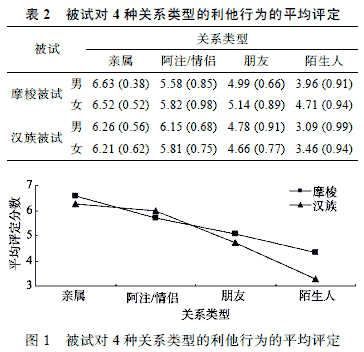中国人研究的沿革、趋势与理论建构
李宇 1,2王沛 1孙连荣 3
摘要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及其的感知与理解。根据对象可以分为认知、人际认知、以及以社会决策为核心的社会事件认知。针对以上四个方面,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为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研究做出了先驱性贡献。但无论就理论建构、研究范式还是研究内容而言,大量研究沿袭了国外研究的预设前提与范畴,即“”,脱离了中国人社会认知滋长的基础——以“差序格局”为基调的传统文化以及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转型期的文化。通过梳理与整合涉及社会认知主题的研究及其内在逻辑,发现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根本特点为“”,并且集中体现为“差序格局”文化衍生与发展的“群际认知()”,进而尝试围绕“群际认知”这条主线解读与建构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推进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深层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社会认知; 本位认知; 他位认知; 群际认知; 阶层认知
分类号 B849:C91
1、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回溯:两种研究意识与三个发展阶段
社会认知是指个体对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及其关系的感知和理解(庞丽娟,田瑞清,2002)。社会认知的对象可分为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以及社会事件认知(包括社会归因、社会推理与社会决策等)。社会认知研究作为与结合的产物,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90年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如今业已成为社会心理学、乃至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且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
面对国际社会认知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中国心理学家们,甚至社会学家们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总体来说,中国心理学界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脉络及其发展轨迹大略呈现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介与初步验证。20世纪80年代末,儿童社会认知领域是社会认知引入中国的最早的领域之一,包括道德发展、儿童攻击性以及儿童间的冲突(顾援,陈会昌,1988;方富熹,1986)。与此同时,开始关注研究(黄希庭,时勘,王霞珊,1984);张智勇(1989)最早介绍了刻板印象的测量与理论研究。自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将研究视角于社会认知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具体研究主要涉及下
述主题:(1)自我认知。包括自我概念(周国韬,贺岭峰,1996;俞国良,翁亚君,1996)、(张文新,1997;黄希庭,张进辅,张蜀林,1989;刘明,1998;魏运华,1998)、自我监控与调节(章建跃 , 1998; 董奇, 周勇, 1995; 刘儒德 , 陈琦, 1999)等;(2)人际认知。主要体现为人际关系 (黄希庭等 , 1984; 章志光 , 王广才 , 季慎英 , 1982)、人际信任与人际冲突 (张荣娟 , 李文虎 , 胡芸, 2005; 张建新, Bond, 1993); (3)群际认知。包括民族冲突 (孙代尧, 1999)、社会认同 (张莹瑞 , 佐斌, 2006)、刻板印象(王沛, 1999)与偏见(王沛, 1998)等; (4)社会决策认知。包括风险决策 (刘霞, 潘晓良, 1998)、组织群体决策 (滕桂荣 , 1988; 刘翔平 , 1996)、道德决策与儿童决策特征 (陈单枝, 朱莉琪 , 2005)等。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以中国被试为对象 , 采用西方的研究范畴、方法以及工具进一步验证国外有关社会认知的理论与研究范式。
第二阶段, 探索与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特征。在第一阶段的研究基础上 , 有些学者发现中西方社会认知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例如 , 利用自编问卷调查我国大学生的自我意识 (韩进之, 杨丽珠, 魏华忠, 1987); 编制一系列中国人自己的问卷, 对中国人的自我 (包括自信、自立、自强、自尊等)进行了探索 (郑剑虹 , 黄希庭 , 2007; 黄希庭 , 余华, 2002; 毕重增, 黄希庭 , 2009; 夏凌翔, 黄希庭, 2008, 2009; 郑剑虹 , 黄希庭, 2004);研究时发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自我参照效应的特点 (戚健俐 , 朱滢, 2002; 刘新明 , 朱滢, 2002); 研究决策时发现中西方存在许多差异 (刘永芳, 苏丽娜, 王怀勇, 2011;段婧, 刘永芳, 何琪, 2012; 马剑虹, 王重呜, 王钢, 郑全全 , 1992; 汪祚军 , 李纾, 2012a, 2012b; 于窈, 李纾, 2006; 张文慧 , 王晓田 , 2008; 郑全全 , 郑波, 郑锡宁 , 许跃进, 2005)。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要将中国独特的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形势结合起来 , 力促社会认知研究的中国化。但就总体而言 , 这个时期的研究显得庞杂而纷乱 , 仅有少数课题涉及到了文化因素(景怀斌, 2006;侯玉波, 朱滢, 2002;凌文辁 , 郑晓明, 方俐洛 , 2003)。且有相当一部分领域仍属于空白 , 例如群际认知领域对阶层认知的研究很少有心理学家涉及 , 倒是有一部分社会学研究者在理论上进行了很有启发价值的探讨 , 开展了有关阶层意识与阶层分化发展状况及其趋势的研究 (陆学艺 , 2002;李路路 , 2012;李培林 , 2005)。
第三阶段, 尝试建构中国化社会认知的研究框架。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 , 心理学家们开始将文化因素纳入各自的研究领域 , 尝试提出他们的中国化理论。例如 , 杨中芳和彭泗清 (1999)率先提出了理解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理论框架。黄希庭和夏凌翔(2004)构建了颇具我国文化传统的特征理论。朱滢 (2007)提出, 中国人的自我不同于西方人的自我 , 前者是互倚的、联系的自我。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部分资深的心理学家们关注到了与西方价值观迥异的对于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 进而呼吁建立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研究之路, 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无疑 , 这些研究活动对于我们构建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理论起到了奠基与导向作用。
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趋势恰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 “意识” (杨波, 1999)的萌发、冲突与调和的变化轨迹。而这两种意识也正是本研究试图构建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下面我们对此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方面,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网络拉近了全世界人们的距离 , 致使人类共性特征与问题的探索与解决成了可能。这种全世界人们都来关注与努力解决共同的重大问题的意识就是所谓的全球意识。就社会认知领域而言 , 全球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研究构想上 , 社会认知心理学家对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应有一个全球眼光, 认识到人类生活有许多共同的主题 , 其理论有着一种整合统一的趋势 , 其研究需要遵循共性原则, 进而联合东西方心理学家 , 共同探索普遍而稳定的社会认知理论模型。二是在研究策略上 , 要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范式与研究工具 , 来考察人类的社会认知特征。
另一方面, 世界文化在破除 “欧洲中心论”之后, 在“全球意识”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而“寻根意识 ” (即“民族意识 ”)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中也就悄然兴起。所谓的寻根意识或民族意识指的是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探究各民族独特的国民心理特征的意识。对于中国来说 , 五千年文化的传承深深铸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特征 ; 国内当前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迁以及因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出现的文化转型 , 国人的社会认知迫切需要重铸与更新。与此同时 , 在国际上, 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当今中国经济的腾飞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盛行等多种原因 , 东方文化,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 中国的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寻根意识亟须增强。
从以上分析来看 , 中国心理学家们在经历了 “全球意识 ”兴起、“寻根意识”的萌发与增强、并与“全球意识”抗衡的阶段之后,势必呼唤二者的调和!因此,无论从学术、社会形势还是文化传承来看,建构中国人特有的社会认知整合体系势在必行,不仅为前瞻和重铸未来中国人社会认知提供一个科学的参考体系,更有助于整合中西方不同的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现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证据。此举显然具有深刻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2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衍变
根据各种社会刺激的类属及其本质,将从四个方面来评述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衍变:自我层面的认知、人际层面的认知、群际层面的认知以及裹缠着社会归因与社会推理的社会决策。
2.1中国人的自我认知
正像Allport (1981)指出的, 自我意识具有个人隐蔽性 , 同时又具有渗透性、弥漫性 , 因而对于隐蔽的自我意识的探索往往只能通过其渗透的、弥漫的作为行为主体的自我外部表现的研究才能达到。离开最能反映自我意识程度、水平的外部行为调节去研究对自我的认识程度、水平 ,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 国外的学者们根据可观察的外在行为表现来研究自我。纵观他们的研究发现 , 西方人的自我受其自身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个人主义文化观驱动下 , 自我研究的预设前提为自我本位, 即强调尊重自我 , 尊重自我个性 , 特别强调自我的独立性、自主性 , 以自己的立场为中心去判断、去行动以强调自我的独特性 , 自我本位的理想模式是和谐状态下的自我实现 , 盲目的极端模式则是自我凌驾于善恶等价值观之上。面对国外的这一理论预设 , 中国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又是如何的呢?
研究早期, 在行为层面的外显认知领域, 研究者直接采用国外认知操作范式的内容来探索儿童在认知操作活动中的自我监控能力 (沃建中 , 林崇德, 2000)。上世纪 80年代, 黄希庭等人采用 (1989)Roeach编制的 “价值调查表”对我国学生的价值观进行了调查。俞国良等人 (1996)采用福托斯编制的田纳西自我概念修订版考察 10~15岁学习不良儿童自我概念发展的性别差异和年龄特征。在内隐认知领域 , 研究者结合自我报告量表与 IAT测验考察了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之间的关系 (蔡华俭 , 2006, 2003a, 2003b; 蔡华俭 , 杨治良 , 2003)。在神经生理层面 , 研究者介绍了西方的面孔识别神经机制研究进展 ; 并利用其范式对自我与他人的面孔识别进行了 ERP实证研究 , 发现自我面孔识别涉及前额叶、脑岛、扣带回等脑区的协同作用 (彭小虎 , 王国锋, 魏景汉, 罗跃嘉, 2004; 关丽丽 , 齐铭铭 , 张庆林, 杨娟, 2011;彭小虎 , 罗跃嘉, 魏景汉 , 王国锋 , 2003)。也有学者介绍了国外自尊领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进展 (尹天子, 黄希庭, 2012; 杨娟, 张庆林, 2010)。
在引介与验证西方研究的基础上 , 学者们他们开始从各自的领域探索中国人特有的自我认知 (张进辅, 童琦, 毕重增 , 2005; 冯冬冬, 陆昌勤, 萧爱铃 , 2008;韩晓燕 , 迟毓凯, 2012; 金盛华 ,郑建君, 辛志勇, 2009; 彭彦琴 , 江波, 杨宪敏 , 2011;王永丽 , 时勘, 2004)。在人格领域 , 编制了中国人自我价值观量表、自立人格量表与青少年理想身体自我量表等 (夏凌翔 , 黄希庭 , 2008; 陈红, 冯文锋, 黄希庭, 2006; 黄希庭 , 余华, 2002); 提出了颇能反映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格特征的关照的 “自立、自信、自尊、自强 ”等自我特征 (胡金生 , 黄希庭, 2009; 夏凌翔 , 黄希庭, 2012)。在记忆领域 , 发现了中国被试参照父亲、母亲进行加工的成绩与参照自己一样好 , 支持了独立型 /依赖型自我概念模型中东方文化下的自我概念包括父亲、母亲、好朋友等十分亲近的人的观点 (戚健俐 , 朱滢, 2002; 刘新明 , 朱滢, 2002)。在中国人的 “自我”概念中, “自我”一词除了代表自己外 , 还代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父母、朋友 (管延华 , 迟毓凯,2006)。一项有关自我面孔识别的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 , 只有中国被试出现了典型的 “Boss– Effect”, 即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自我面孔 , 而美国被试则出现了自我面孔优势效应 (马建苓, 陈旭, 王婧, 2012; Liew, Ma, Han, & Aziz-Zadeh, 2011)。研究者还在自我研究中发现 , 中国人可能拥有在社会情境与自我之间寻求均衡点的中庸自我 (林升栋, 杨中芳, 2007)。习惯于阴阳关系思维的中国人会称他们的 “自我”是“既此又彼 ” (如“外圆内方”、“刚柔并济 ”), 而且并不感到 “自相矛盾 ”。中庸自我能够看到对立两极之间的转化关系 , 他们在感知与行动方面的差异并不是为了博取社会赞许, 而是基于 “诚”的修养。研究者提出 , 中国人一方面仍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若干心理与行为特征, 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西方现代工商社会中的若干心理与行为特征 , 合而成为一种兼具心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双文化自我。他们构想了一套华人双文化自我的个体发展的阶段理论 , 包括个体取向的自我发展五阶段理论与社会取向的自我发展五阶段理论相结合的 Y型架构 (杨国枢 , 刘奕兰, 张淑慧, 王琳, 2010)。
在神经科学领域内 , 中国学者也找到了一些具有中国化的自我认知特征的证据。朱滢(2007)对记忆领域内的自我结构的研究较为系统。他强调西方哲学、西方心理学与西方 (被试的 )神经科学这三个层面在自我概念(结构)上是一致的, 都突出个体的自我自身 , 反映在大脑活动上 , 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不表征母亲。中国哲学、中国心理学与中国 (被试的 )神经科学这三个层面在自我概念(结构)上也是一致的, 都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的联系 , 反映在大脑活动上 , 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在自我面孔识别的神经机制研究中 , 研究者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简称 ERP)记录了英国和中国被试判断自我面孔和熟悉面孔头部朝向时的脑电反应 , 结果表明对英国被试来说自我面孔更容易引起注意 (Sui, Liu, & Han, 2009)。研究还发现 , 两种文化下所产生的脑电显著不同:英国被试在知觉自我面孔时在额中区产生了 N2 负波; 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才产生较强的 N2负波。N2反映了那些与自我相关的有意义的面孔的深度识别(Folstein & Van Petten, 2008)。对此, 研究者认为 , 现有的脑成像技术坚实地证明了不同文化中自我的经验与概念化方式之间存在差异。东亚文化环境对个体间联结的重视导致了自我与亲密他人在神经表征上的融合 , 而西方文化中独立型自我的主导地位促进了自我与他人在神经表征上的分离 (杨帅, 黄希庭, 王晓刚 , 尹天子, 2012)。
从以上有关中国人自我认知的研究来看 , 在早期对西方理论与研究范式验证性研究的基础上, 国内学者的寻根意识逐渐萌生并形成与全球意识抗衡的趋势 , 为中国化的自我研究做出了先驱性贡献, 但还没有构建起与文化相整合的自我理论框架, 因而无法根本性地解决一些核心问题 , 包括:中国人自我的本质及其结构是什么?是强调个人取向、人际取向还是社会取向?为此 , 我们应着力探索中国人自我认知的本土化理论和方法 (杨帅等, 2012)。
2.2中国人的人际认知
人际认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的探索上。所谓人际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是指人与人在交往中建立的直接的心理上的联系。在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过程中 , 竞争与合作是两种最基本的人际互动行为模式。西方的科学家们常常借助博弈论、 “合作-竞争 ”游戏等范式来探讨人际认知过程的行为与神经机制 (刘长江, 郝芳, 2011)。这方面有关人际互动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普遍发现:人际信任是个体合作行为模式发生的基础(Balliet & Van Lange, 2013; Barczak, Lassk, & Mulki, 2010; Lewis & Weigert, 2012; Tariq, Aslam, Habib, Siddique, & Khan, 2012)。同时,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 , 简化了复杂的社会认知 , 具有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秩序的功能 (朱虹, 2009)。但是, 西方的这些研究都是以其文化与价值观作为基础的 , 他们更强调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国人的人际认知是否也是如此呢?
国内学者初步研究了中国人的各种人际关系 , 包括同伴关系、配偶关系、亲子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赵志裕, 邹智敏 , 林升栋, 2010; 李梅, 卢家楣, 2005; 刘嘉庆, 区永东 , 吕晓薇 , 蒋毅, 2005), 发现维持上述关系的核心因素是人际信任 (郑晓涛, 柯江林 , 石金涛 , 郑兴山, 2008; 池丽萍 , 辛自强, 2003; 李幼穗, 赵莹, 2009; 孙晓军, 周宗奎, 范翠英 , 柯善玉 , 2009; 王美萍 , 张文新, 2007; 沃建中 , 林崇德, 马红中 , 李峰, 2001; 张晓, , 张桂芳, 周博芳 , 吴巍, 2008)。我们团队采用“取消惩罚 ”范式, 发现虽然惩罚对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 , 但是必须通过人际信任才能影响合作行为(王沛, 陈莉, 2011)。因此, 我们初步推断人际信任对于中国人的人际互动过程也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
针对中国人的信任研究发现 , 中国人所说的信任往往包括人际互动对象先天的及后天的连带关系及人情 , 而非西方人所看重的他人因能力和责任感获得的信任 (杨中芳, 彭泗清 , 1999)。换句话说, 对于信任的具体研究需要考虑心理、社会与文化三重含义。结合中国文化与社会模式 , 人际纽带是中国化信任的发生基础 ,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是 “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 (朱虹, 2009)。在引入“关系”的基础上 , 有研究者提出了中国人信任的三阶段模型 (韩振华, 2010), 即生人、熟人与家人三个不同的阶段其机制也各不相同。另外 , 中国人强调个人通过实践诚信来赢得他人的信任, 同时对熟悉的人自然而然地怀有信任感 , 这也与西方信任完全不同(吴继霞, 黄希庭, 2012)。
综上所述, 国内对人际认知的早期研究更多地是遵循西方的研究路线 , 无疑也认同了西方的文化观与价值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 研究者发现中国人的人际认知紧密贴近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形势。在人际互动的核心因素 —信任的研究中 , 已经表现出了中国化的特征。即, 不同的关系决定着各种人际信任的表达方式及其水平。那么, 接下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系统探讨:这些人际信任的表现方式及其不同水平是否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人的人际互动过程?其作用机制与西方人的人际信任有何异同?显然 , 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 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 而且有利于促进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世界的关系, 实现心理和谐、社会和谐。
2.3 中国人的群际认知
西方有关群际认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30年代的移民运动以及种族之间的敌视 , 诸如马丁被刺事件引起了社会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 群体偏见及刻板印象问题随即出现。人们开始反思群体之间的关系 , 尤其是种族之间的关系。同时一批批新的移民不断涌入西方国家 , 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程序。如何实现民族之间的认同, 减少并消除种族冲突 , 以及如何促使新移民融入社会 , 这些关系到西方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成了政府、学者以及社会各届人士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 加上西方国家崇尚的 “人人平等”的文化价值观的推波助澜 , 社会心理学领域兴起了群体心理学研究热潮 , 集中体现为对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污名化、群体认同以及群体冲突的研究 , 旨在解决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但是上述研究 , 无论理论与研究范式发展得多么完善 , 究其根本 , 仍然体现着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自我本位 ”, 即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上考察该群体对自身的积极偏见、对其他非主流群体的消极偏见 , 关注其他群体如何改变促使其获得主流群体的认同 , 并最终实现群体间的平等。
而国内早先的群际认知研究、甚至当下大多数群际认知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刻板印象与污名效应。上世纪 80年代, 张智勇(1989) 最早将刻板印象研究引入国内。杨治良、王沛等人较早地对刻板印象进行了外显行为层面的研究 (王沛, 陈学锋, 2003), 他们采用回忆 —练习范式和再认范式探讨了刻板印象表征中的信息组织模式及其功能 (王沛, 杨亚平 , 2007)。其后 , 以杨治良所领导的研究团队为核心 , 引介并改良了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杨治良与连淑芳等人 (刘素珍 , 杨治良 , 龚佃祥, 赵华, 1998; 连淑芳, 2006; 连淑芳, 杨治良, 2007)发现刻板印象除了控制加工方式之外还存在着自动化加工方式。梁宁建与王沛等人也采用国外的内隐研究范式 , 如 IAT与刻板解释偏差测量等检验了刻板印象的内隐效应 (俞海运, 梁宁建, 2005; 王沛, 孙连荣, 2007)。俞国良、王沛等人尝试探索艾滋病人等群体的污名化问题 (张宝山, 俞国良 , 2007; 杨金花 , 王沛, 袁斌, 2010; 杨金花, 王沛, 2011)。在以上行为研究的基础上 , 他们进一步对性别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讨 , 发现了标志着冲突情境中刻板印象激活效应的脑电特异性成分 (王沛, 杨亚平 , 赵仑, 2010; 杨金花 , 王沛, 2011)。但是 , 由于研究设计和被试样本的限制 , 此类研究未能触及到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内核 , 其理论诉求依然是验证国外提出的理论模型或相关结果。
除此之外, 还涉及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内容—阶层认同。尽管阶层认同当前已然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 , 但仅引起了少数社会认知心理学家的重视(陈加州, 凌文辁, 方俐洛, 2003)。相反, 社会学家们却比较关注这个课题。他们通过调查发现 , 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周晓红 , 2005; 仇立平 , 顾辉, 2007;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 "课题组, 2004; 李春玲 , 2004; 刘精明 , 李路路, 2005; 陆学艺, 2002)。阶层认同的不一致以及我国贫富差距形势的迅速扩大 , 阶层冲突逐渐凸显。李培林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 , 阶层认同决定了人们社会冲突取向:中国当前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类型 —社会价值观念性矛盾是导致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李培林, 2005)。另外, 值得关注的是, 近年来民族之间的冲突暨族际冲突已悄然成为国内阶层冲突不可忽视的特例 , 例如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的民族冲突逐渐影响着中国的安定团结与国家统一, 成为影响我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最为突出的问题。研究民族认同迫在眉睫 (万明钢, 王亚鹏, 2004; 张世富 , 阳少敏 , 2003)。对于族际冲突的本质问题 , 刘力等人则发现 , 民族冲突形成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致 , 而是基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和社会情境层面的多水平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刘力, 杨晓莉, 2011)。到目前为止 , 国内社会学界有关阶层认同、阶层冲突与族际冲突的研究水平相对较低 , 研究方法单一、精确性低, 研究结果莫衷一是。
纵观国内已有的群际认知研究 , 最大的特点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沿用了西方的模式 , 其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是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 (刘欣, 2001), 并没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前的社会形势。另外, 针对国内剧烈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 , 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高度关注 , 却没有引起社会认知心理学家们的足够重视。因此 , 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来建立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群际理论框架。
2.4 中国人的社会事件认知
社会事件认知包括社会归因 (张爱卿, 刘华山 , 2003)、社会推理 (段锦云 , 凌斌, 2011; 侯玉波, 朱滢, 2002; 张结海, Bonnefon, 邓赐平, 2011)与社会决策 (孙彦, 许洁虹 , 陈向阳, 2009; 李超平 , 时勘, 2003; 王宇清 , 龙立荣 , 周浩, 2012; 张红霞 , 李佳嘉 , 郭贤达, 2008)。其中 , 社会决策是核心与最终结果 , 它指的是对社会事件的判断取舍 , 是人的社会认知的终极结果。西方文化强调运用公平、公正 , 依赖社会不偏不倚的原则、标准和规范来解决社会问题 ; 个体之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 人与人之间彼此是平等互惠的。基于这种 “自我本位”取向的文化观 (汪祚军, 李纾, 2012b), 西方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往往以自我为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决策研究范式是封闭型的 , 即决策者只有主体本人 , 不受其他人影响。他们关注的是在利益得失之间思考 “如何对我最有利? ”。那么, 国内学者在决策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呢?
李纾等人对风险决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孙悦, 李纾, 2005; 李跃然, 李纾, 2009; 汪祚军, 李纾, 2012a, 2012b)。他们以中国人为被试对西方的风险决策研究进行检验 , 发现与西方的理论并不一致 , 建议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例如, 他们基于信息加工过程视角 , 采用眼动技术检验风险决策整合模型和占优启发式模型 , 发现实验所得到的结果无法用西方的累积预期理论为代表的整合模型或占优启发式模型来解释。为此 , 他们基于齐当别视角 , 建议采用多角度、多指标的方式来探讨人们的决策过程 , 进一步检验、修改、完善以及建立新的启发式模型或决策过程模型 , 以便更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进行风险决策的。值得注意的是, 李纾等人在介绍西方的决策者—建议者系统模型时提出需要开展跨文化研究(李跃然, 李纾, 2009)。李红等人将成人的风险决策研究拓展到了儿童群体 , 从认知发展角度研究了不同年龄儿童决策的特点、趋势以及影响因素 , 进一步促进了风险决策的发展理论研究。例如 , 他们考察了儿童完成最后通牒博弈决策的发展特点 (陈璟, 孙昕怡, 李红, 2012); 探讨了观点采择因素对 3~4岁儿童延迟满足决策的影响 , 发现随着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 , 儿童逐渐能够确立正确的延迟动机, 为他人做出有效的决策 (蒋钦等, 2012);等等。刘永芳则研究了职业决策 , 他利用信息板技术考察了成就动机对职业生涯决策过程中风险偏好的影响 , 发现成就动机和任务框架的交互作用对职业决策风险偏好有显著影响(王怀勇,张娜,刘永芳, 2010) 。
在认知神经科学层面上 , 李红等人运用脑电技术考察了决策后的反事实思维过程 , 发现 FRN和 P300是对反事实思维敏感的 ERP成分, 且 ACC可能是调节反事实思维的重要神经结构 (王会丽等 , 2010)。李健、王艳和唐一源 (2011)对道德两难冲突情境下的神经机制研究表明 , 随着道德判断的进行 , 差异性的电活动从双侧颞枕区向前额中区延续 , 高道德违背情境会更强地抑制额区和额中央区等的电活动。
不可否认, 李纾等人的研究发展了决策领域的研究 , 填补了国内决策领域的空白 , 对中国社会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作用。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的前提同样遵循了西方的 “自我本位”的文化预设 , 采用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封闭式决策模式。尽管已有部分学者考虑到了决策者为他人作决策的模式 (刘永芳, 陈雪娜 , 卢光莉, 王怀勇, 2010; 段婧等 , 2012), 为中国化决策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 但这也仅仅处于 “自我”决策到 “自我—他人”决策的过渡阶段 , 并没有真正体现中国文化中的 “他人本位 ”。所谓的他人本位 , 即与自我本位相对, 指的是站在他人 (包括个体他人、家族、国家民族 )立场作出判断、作出行为 , 关注外在的道德行为标准 , 重视与他人之间的联结 , 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利益而优先满足他人 (尤其是家族、民族与国家 )利益。对中国人社会决策的心理实质而言 , 需要思考自我、人际、群际互动对决策的影响 , 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中国人更看重名还是利 , 当代中国人以名誉、责任为重的社会模式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其心理机制如何?如何培养高尚的荣誉感与责任心?因此 , 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领域的社会决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3、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理论体系建构 — “他位认知”取向的视角
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 ”指出: “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 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 , 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 ,健全网络, 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 “决定”中首次阐述了社会和谐与心理和谐的关系。对于中共中央文件来说 , 如此论述心理学问题还是第一次。这不仅对我国心理学工作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 而且对于我国心理学界实现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努力提供了重要契机。
然而从当前有关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现状来看, 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 从学科本身的理论基础来看, 国内学者的社会认知理论基本上遵循的是西方的理论观点。这等同于默认了隐含其理论背后的西方文化预设—“自我本位”取向作为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理论前提 , 显然无法解释具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中国人的 “他位”取向的社会认知现象 , 更谈不上揭示中国人所特有的社会认知特征了。其次 , 从研究范式来看 , 随着社会认知的蓬勃发展 , 研究范式不断更新以适应并推动学科的快速发展。尽管如此 , 这些研究范式是服务于学科的理论发展需要的 , 适合于西方理论框架下的研究需要。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社会认知理论 , 因而缺乏适合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再次 , 从研究范畴来看 , 许多学科的研究者已经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开始了中国化的研究。诸如中国人独特的自我、社会阶层与族际冲突等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于研究中国人社会认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 不仅具有独特的中国文化传承 , 并具有深刻的中国社会变迁的烙印 , 而我们的社会认知心理学家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最后 , 从学科的发展来看 , 研究者们不仅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关注中国人社会认知领域中群际与人际范畴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水平机制 , 而且也开始关注该领域中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水平的认知机制 , 甚至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神经水平上的脑机制乃至与分子水平的生理机制。这就促使中国人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迫切需要展开跨学科的合作与整合。
以上存在的问题 , 结合中国人的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历程 , 正是文中前面所述的两种意识发展的体现 , 即中国学者在全球意识的 “一边倒 ”基础上逐步萌发了 “寻根意识 ”。随着 “寻根意识 ”的加强, 引发了两种意识间的冲突与抉择问题。这两种意识之间的冲突能否调和 , 以及如何调和?我们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高屋建瓴式的蕴含文化因素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框架。换句话说 , 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研究首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构建符合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同时又合乎社会认知研究走向的中国化的社会认知理论框架。为此 , 我们尝试结合中国文化的“他位取向 ”构建适合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认知的理论框架(见图 1)。
3.1自我认知的衍变
与西方文化下的独立性 “自我”不同, 最近有研究初步验证了中国文化下的自我是个人自我、关系自我与集体自我的合集 , 并且从外显和内隐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三种取向的自我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李昌俊, 2010)。
那么, 中国人的自我是否是这三者的合集呢?我们认为自古以来 , 中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 , 强调克己利人、修身养性。《论语·雍也》中说: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 是崇高的人生理想。从仁的本旨派生出两层含义 , 一是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 , 二是协调人际关系。这里的 “立”与“达”的目标是自己求立 , 并使人立 ; 自己求达 , 并使人达。将自己与他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 成人成己才是我们的追求。而宋朝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一句话备受国人推崇: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把天下、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 , 将个人的名誉与天下、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相连。当代心理学家黄希庭也指出:我国传统文化看重社会和谐 , 人际共存 , 个人决不能离开他人而生活 ; 强调个人承担社会角色义务 (岳彩镇, 黄希庭, 岳童, 2012; 岳彩镇, 黄希庭, 2012)。这就意味着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不能仅仅从自我本身出发 , 更要关注与自我关系密切的重要他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说 , 中国人对 “自我”的理解实质上隐含着 “差序格局 ”的存在。正如 Markus和 Kitayama (1991)指出,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下 , 人们往往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结构 , 由此涉及自我的所有加工过程都将采取不同的形式 (Markus & Kitayama, 2003);一旦自我的信息加工不同 , 其相应的神经机制亦将采取不同的形式 (Zhu & Han, 2008; Zhu, Zhang, Fan, & Han, 2007)。
因此, 我们认为, 中国特有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观 , 即中国人的自我具有依存性, 体现在个体我、关系我与群体我三个成分一体化的 “家国观”中。其中 , “我”认知即个体自我认知, “家”认知是指以重要他人为轴心的关系自我, “国”认知则表现为以族群和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群体自我 , 三者以与我关系远近的差序格局排列, 体现了“差序”的观念, 无论个体我还是关系我都蕴含于群体我之中。研究构思如下:
研究1 中国人自我认知的特点: “我—家—国” 的认知与大脑同构性
首先对各年龄阶段、各地区的社会公众进行访谈, 收集自我、重要他人和国家的关联词和特质词, 编制中国人自我认知结构量表 , 作为以下研究的材料。然后通过三项研究来探讨自我认知结构。需要说明的是 , 在被试的选取上 , 初期选用大学生被试 , 其后分别从社会阶层、年龄和经济带(即居住区域 )三个方面考虑选取被试。操纵社会阶层变量旨在考察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 (较高、中间、较低)在社会认知中的各自表现是否存在差别。操纵当前年龄变量 (60岁以上老年组、 35~45岁中年组、 18~25岁青年组 )旨在考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同程度影响的被试的社会认知差异。操纵经济带变量 (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发展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 )旨在更全面地反映当今中国各经济发展区人们的社会认知差异。
子研究 1:中国人自我认知的 “我—家—国”结构:不同自我认知加工的同源性研究
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国人自我认知的 “我—家 —国”结构, 即不同自我认知加工的同源性。实验 1采用自我参照效应的 R/K研究范式 , 考察不同类型的中国人 (年龄、阶层、文化经济带 )在不同参照条件下 (自我与他人、重要他人与一般他人、本民族国家与外族国家 )对相关词语与符号刺激的认知加工的异同 ; 实验 2采用事件相关电位 (ERP)研究技术, 考察不同类型的中国人 (年龄、文化经济带、阶层 )在不同参照条件下 (自我与他人、重要他人与一般他人、本民族国家与外族国家 )对相关词语与符号刺激加工的大脑神经活动特征 ; 实验 3采用 fMRI技术考察不同类型的中国人 (年龄、文化经济带、阶层 )在不同参照条件下 (自我与他人、重要他人与一般他人、本民族国家与外族国家)对相关词语任务判断时 , 大脑内侧前额叶 (MPFC)的激活程度上的差异。
子研究 2:中国人“我—家—国”自我认知结构的内部关系与群体差异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人 “我—家—国”自我认知结构的内部关系与群体差异。实验 1采用自我表征分类技术, 将个体自我、重要他人和民族 (国家)相关的概念和符号进行自我表征符合程度的分类判断 , 并采用多维关系剖面图分析 (Profile Analysis)方法计算它们与个体自我表征的心理距离, 以此来说明它们在自我认知结构中的远近与关系; 实验 2、3、4分别采用行为、 ERP技术与 fMRI技术, 使用课题组编制的中国人自我认知结构量表, 考察不同类型的人群 (经济带、年龄、社会阶层 )在不同参照条件下 (自我与他人、重要他人与一般他人、本民族国家与外族国家 )的认知加工过程中行为特征、大脑活动过程与激活脑区的异同。
子研究 3:中国人“我—家—国”结构的融合策略:启动与内隐联结效应
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人 “我—家—国”结构的融合策略。实验 1采用内隐社会认知范式 , 以自我、重要他人、国家相关词语或图片为刺激材料 , 考察与一般他人、外民族国家相比 , 中国人有关个体自我、重要他人与本民族国家的内隐联结效应的异同 ; 实验 2采用阈下启动范式 , 通过内隐联想测验比较实验组 (启动)与控制组 (无启动 )在自我与重要他人、自我与民族国家概念在内隐联结效应上是否存在差异 ; 两组在人际信任与国家认同上是否存在差异 , 以此来探索促进中国人 “自我—家—国”积极融合的无意识策略有效性 ; 实验 3采用 ERP与 fMRI结合技术 , 使用阈下启动范式考察实验组 (启动)与控制组 (无启动)在自我与重要他人、自我与民族国家的内隐联结效应中大脑活动的时间过程及脑区活动特点 , 检验无意识启动在促进中国人 “自我—家—国”积极融合的有效性 ; 实验 4采用 fMRI技术比较在不同文化价值观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启动条件下在自我、重要他人和国家认同判断任务中的脑区激活特征, 检验文化价值观启动技术在促进中国人 “自我—家—国”积极融合的有效性。
3.2 人际认知的衍变
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于人际互动的基础 —人际信任的表现形式及其水平有着重大影响。中国一直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的等级社会 , 强调克己利人, 追求在社会归属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交往。其人际信任的获得方式往往体现为 “长幼有序”、“上下有别”式的“各就其位”, 即通过建构各种各样的阶层关系来谋求人际信任的维持。如此 , 中国人的人际互动模式必然表现出与西方人迥异的“他位主义”取向—首先需要考虑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关系, 然后启动与之相对应的人际信任类型。也就是说 ,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具有浓厚的阶层归属特色, 反映的是人际间纵向的阶层关系。这与西方文化的主张截然相反 , 如此势必会造成中国人的人际互动过程有别于西方。
具体来说, 因阶层关系的不同,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会具体体现为: (1)与下位他人交往时 , 中国人需要通过仁爱表达人际信任。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 , 非人也。恻隐之心 , 仁之端也。 (2)与平位他人相处时讲求信任。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论语 .学而篇》 )。诚如曾子所言 , 此处的信任是指与朋友交往要让朋友信任我们, 而非西方文化所倡导的 “对别人信任”式的人际信任。 (3)与上位他人相处时讲究忠孝。①对待长辈要孝。儒家学者一直主张: “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 皆能有养。不敬 , 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当代学者的研究也表明, 孝道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具有稳定的核心作用(任亚辉, 2008;范丰慧, 汪宏, 黄希庭, 史慧颖, 夏凌翔, 2009)。②对待上级和组织要忠诚。由于中国文化强调上下间的秩序与角色规范 , 下位者必须服从上位者的要求 , 因此, 部属对上司的忠诚在上对下的信任中就显得重要。有研究者强调 , 《论语》中有 13种重要的人际交往行为是受到特别称许的, 其中屈从权威(包括顺从父母、长辈及上司等上位者的要求)居于首位(郑伯, 1999)。
因此, 我们认为对中国人的人际认知的建构始于对 “他人”的社会身份识别 , 同样体现了 “差序”观。中国人往往根据他人身份与自我的阶层差序, 启用相应的信任类型。与下位他人的交往遵循仁爱模式; 与平位他人的交往遵循信任模式 ; 与上位他人的交往遵循忠孝模式 , 其中与亲缘关系的上位他人相处遵循孝顺模式 , 与业缘关系的上位他人相处遵循忠诚模式。如果信任关系处理适宜则产生合作行为 , 处理不当则可能出现竞争与冲突行为。研究构思如下:
研究 2:中国人的人际认知: “他位”取向对合作和竞争的影响
子研究 1:中国人人际信任量表的编制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找出中国人与不同阶层 (上位/平位/下位)的人交往时各自遵循的人际信任类型, 并编制信任量表。
子研究 2:社会阶层与信任水平影响最后通牒任务中合作的认知神经机制
本研究采用最后通牒任务旨在考察社会阶层与信任水平对人际合作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实验 1将反应者与提议者 (由实验助手扮演 )的阶层区别(上位/平位/下位, 反映了对应的信任类型 )作为自变量 , 记录被试对提议者呈现的提议作出反应时的行为与大脑活动指标 (ERP技术与 fMRI技术结合), 考察阶层影响人际合作的动态认知神经机制。实验 2将反应者与提议者 (由实验助手扮演 )的阶层区别、被试对所呈现的其他三种阶层人物的信任水平(使用编制的信任问卷 , 区分为高信任 /低信任)作为自变量 , 记录被试对提议者呈现的提议作出反应时的行为与大脑活动指标 , 考察阶层(即信任类型 )与信任水平影响人际合作的动态认知神经机制。
子研究 3:社会阶层与信任水平对合作与竞争的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
本研究采用斗鸡博弈任务旨在考察社会阶层与信任水平对人际合作与竞争的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实验 1将被试与一起游戏的对象的阶层区别作为自变量 , 记录被试反应时的行为与大脑活动指标 , 考察阶层影响人际合作与竞争的动态认知神经机制。实验 2将被试与一起游戏的对象的阶层区别、被试对游戏对象的人际信任水平作为自变量 , 记录被试反应时的行为与大脑活动指标 , 考察阶层及其信任水平影响人际合作与竞争的动态认知神经机制。
3.3 群际认知的衍变
以往有关群际认知的研究相当一部分都围绕着西方以平等为最终目标的 “自我本位”群际观而展开。显然 ,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生存环境截然不同 , 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剧烈文化变迁及社会转型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也相差甚远。众所周知 ,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差序社会 , 其群际关系根本特征表现在上下有别的阶层关系上 , 因而中国人的群际认知自然会对阶层关系有很深的体认。换句话说 , 中国人的群际认知必然包含社会阶层认知。尤其对目前来说 , 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 , 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在此背景下 , 中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变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这就使得以往蛰伏于文化传承中的阶层认知又体现出新的特点 (马广海 , 2011)。诸如 , 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 , 阶层认知得到了迅速强化 , 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阶级差别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 , 阶层冲突逐渐凸显。而接二连三的族际冲突问题更需要社会认知心理学家们在学科交叉和方法交叉的层面上探索敏感度高、可操作性强的预警系统。
据此, 中国主要的群际认知问题体现为阶层认知问题。参照有关群际认知的国内外研究 , 我们认为 , 阶层认知可能包括三个操作化的认知成分:(1)阶层觉知。首先要先了解中国人有没有意识到社会阶层 (上位阶层、平位阶层与下位阶层 )的存在, 以及这种主观意识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进一步体现为对他阶层的刻板印象与元刻板印象。 (2)阶层认同。即对自己所属阶层或其他阶层群体的评价。具体表现为:①是否对自己所属阶层具有归属感和悦纳感 ; ②是否出现刻板印象与元刻板印象效价上的极端两极性指向以及内容上的严重分离 ; ③是否出现不可抑制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 ; ④是否出现不可抑制的社会认同威胁效应。 (3)阶层冲突。如果对自己所属阶层评价积极, 则对自己所属阶层具有归属感 , 则表现为阶层和谐 ; 如果对自己所属阶层、特别是对他人阶层产生消极的刻板印象 , 同时其相应的元刻板印象与刻板印象的性质相反、内容严重分离并超出某一程度 , 表明阶层认同失败 , 最终可能导致阶层冲突(以及作为阶层冲突的一个特例 —族际冲突)。我们需要紧密联系传统文化与社会形势 , 将社会学、管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生物学等学科与社会认知心理学结合起来 , 深入研究群际认知的特征与机制 , 构建微观 (如, 社会心理与舆情分析)层面的群际冲突预警系统。
以上对自我认知、人际认知以及群际认知的剖析, 我们可以看到 , 中国文化至始至终都贯穿着“差序”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我们的社会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等级鲜明的有序社会。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将中国社会总结为 “差序格局 ”, 并且将中国社会区分为 “熟人社会”与外围的世界 (即中国人惯常所指的“社会”)(费孝通, 1948)。在 “熟人社会”里, 血缘与地缘合一 , 自我与宗法群体合一; 而在外围世界中 , 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则是各种阶层关系。前者构成了 “家国观 ”的社会文化基础 , 后者则衍生出了浓厚的 “阶层认知 ”。即便是儒家所讲的 “仁爱”、“道义”等体现社会公正的认知标准也都是有社会等差的 , 所谓“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 ”就是这种等差的经典体现。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中 , “差序格局 ”所执掌的“阶层认知”往往以集体偏见的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教育、管理决策等诸多重要的社会实践领域。在教育中、管理和资源分配中 “亲疏有序 ”、“内外有别 ”,高考录取中的地区差异、行业之间利益地方保护以及管理决策都或多或少会受到 “阶层认知 ”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的社会阶层问题将牵涉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 , 无论从文化传承上还是从当前社会形势上来看 , 群际认知都是中国人社会认知的核心因素 , 集中体现着中国文化的 “差序”观与“他位”观, 并贯穿于社会认知始终。本研究包含两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中国人的阶层觉知、认同与冲突研究 ; 第二部分为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族际冲突心理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研究构思如下:
研究 3a:中国人的阶层认知:觉知、认同与冲突
子研究 1:中国人的阶层觉知状况
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调查与实验探讨中国人的阶层觉知状况。研究 1对不同社会成员进行访谈, 获得可能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 , 形成阶层觉知问卷 ; 研究 2按照前面研究划分的社会阶层 , 对不同阶层的群体成员进行访谈 , 获得三类社会阶层的刻板印象词语和元刻板印象词语 , 编制两级特征词表 ; 通过再次调查 , 获得有关阶层刻板印象和元刻板印象的典型特征以及不同阶层成员刻板印象和元刻板印象特征的差异性 ; 实验 3采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 (高威胁 /低威胁/无威胁 )与测验难度(高难度 /中等难度 /低难度)为自变量的被试内实验设计 , 考察社会较低阶层成员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的工作记忆受损情况 ; 实验 4运用 fMRI技术以刻板印象激活状况 (激活/未激活 )为自变量 , 考察社会较低阶层成员在刻板印象激活情境下的工作记忆与非激活状态下 (呈现中性词语)的工作记忆是否存在差异 , 并探讨相应的激活脑区的差异性。
子研究 2:中国人的阶层认同状况
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人的阶层认同状况。研究 1编制不同社会阶层对本阶层和其他阶层的认同问卷 , 比较社会较低阶层和社会较高阶层对本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外显阶层认同状况。实验 2结合 fMRI技术, 采用反应 /不反应联系任务 (GNAT)考察不同社会阶层 (较高阶层/较低阶层)对本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内隐阶层认同状况及其脑机制。实验 3采用改编后的 Stroop启动任务考察不同社会阶层对本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内隐阶层认同状况及其脑机制。
子研究 3:中国人的阶层冲突状况
本研究通过以下 6个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人的阶层冲突。研究 1编制阶层冲突问卷 , 考察考察不同社会阶层 (较高阶层、中间阶层、较低阶层 )对冲突的感知。研究 2采用群体横向调查法和典型案例追踪法 , 针对社会转型期多发的社会阶层之间冲突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 , 考察冲突情境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发展规律 , 系统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冲突形成的原因 (价值性原因、物质性原因 )。研究 3以非阶层冲突者和阶层冲突者(因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等至少参与过一次对抗活动 (如信访、走访政府机构产生冲突等的个体)成员为被试 , 收集关于阶层冲突社会表征的数据,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Pajek)对数据进行可视化网络分析和测量研究 , 在比较非阶层冲突者和阶层冲突者的核心要素和外周要素差异的基础上 , 对焦点个体进行分类 , 结合内隐攻击性测量结果, 来界定阶层冲突预警的典型表征要素。研究 4运用阶层觉知、阶层认同与阶层冲突问卷, 比较非阶层冲突者和阶层冲突者的外显差异。研究 5采用以被试类型 (阶层冲突者 /非阶层冲突者, 被试间变量 )与事件类别 (国内阶层 /国外阶层冲突/中性事件 , 被试内变量 )为自变量的混合实验设计, 以生理指标(心率、肌电、皮电、血容量)和攻击性行为为因变量 , 在此基础上甄别冲突预警指标。研究 6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 将生理驱动因素、认知加工因素、行为动力因素和攻击性作为阶层冲突系统的核心组分 , 建构阶层冲突的心理机制模型 , 同时将生理指标、心理表征要素、行为激活系统、行为抑制系统、攻击性行为作为检测和监测阶层冲突的心理预警指标 , 根据复杂系统科学中的突变级数法来分析鉴别个体的冲突心理行为状态, 构建有效干预方案。
研究 3b: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族际冲突心理预警与干预机制研究
子研究 1:族际冲突的神经生物机制研究
本研究旨在通过静息和诱发两个条件下神经生物特性及其唤醒特性的考察 , 找出变异性较大和稳定的那些生理指标 , 并考察它们的社会心理意义。实验 1以民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藏族/汉族)与被试类别(族际冲突者/非族际冲突者)为自变量的被试间设计 , 首先采集他们的生化数据 (皮质醇和睾丸素), 然后使用多导生理记录仪采集基线生理反应数据 (心率、皮电、脑电与肌电 ), 最后要求他们完成自陈报告测试 (使用问卷完成特质攻击性、反应性 .主动性攻击、行为抑制 /激活系统特性、奖励和惩罚敏感性测试 ), 以此考察静息状态下族际冲突者的自主神经活动特性及其反应模式。实验 2采用民族、被试类别与诱发影片类型(族际冲突影片 /暴力影片/中性影片, 被试内变量)为自变量的混合设计 , 首先采集基线生理反应数据, 接着观看影片并记录生理指标 , 然后采集生化数据 , 最后完成自陈报告测试来考察事件诱发下族际冲突者生理反应模式的特异性 , 以及它们的社会心理意义与预警参考价值。
子研究 2:族际冲突的社会认知机制研究
本研究从社会表征、注意偏向、冲突监控三个方面考察族际冲突信息的认知加工特性。研究 1采用自由联想任务 , 探测不同民族与类别的被试的族际冲突的社会表征特征 ; 实验 2采用民族类别(同上, 被试间变量 )、被试类型 (同上, 被试间变量)与线索词类别 (表征线索词 /中性线索词 , 被试内变量)为自变量的混合设计 , 首先对被试进行生理基线测量 , 接着要求被试完成词汇颜色判别任务, 然后被试完成生理指标 (ERP脑电指标 )、自陈测试后测 , 考察族际冲突社会表征信息的认知加工特性 ; 实验 3采用同实验 2的混合设计 , 运用视觉点探测范式考察族际冲突者加工族际冲突线索的注意偏向特异性及其脑机制。实验 4采用民族、被试类别与图片 -词汇线索类别 (冲突线索 /一致线索 , 被试内变量 , 其中冲突线索由冲突图片 —中性词与中性图片 —冲突词构成 , 一致线索由中性图片 —中性词与冲突图片 —冲突词构成 )为自变量的混合实验设计 , 要求被试进行词汇颜色判别, 记录被试的行为反应以及 ERP脑电数据 , 之后完成自陈测试 , 考察族际冲突线索的认知监控脑机制。将上述子研究 1、2中的测试数据联合分析后找出它们的社会心理意义 , 在此基础上分析它们的族际冲突心理预警指标价值。
子研究 3:族际冲突的行为动力机制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在族际安全困境、社会公平情境下 , 族际冲突的行为特性。实验 1采用民族类别、被试类别与情境类别 (攻击/合作/防御, 被试内变量)为自变量的混合设计 , 实验前先让被试完成自陈测试 , 实验中要求被试对安全困境情境作出决策 , 记录被试的行为反应以及实时生理指标(脑电、皮电与肌电 ), 以考察族际安全困境下的行为动力特性及其生理特征。实验 2采用被试类别、族际类别 (内族/外族, 被试内变量 )与方案公平性(公平/不公平, 被试内变量 )为自变量的混合设计, 实验前先让被试完成自陈测试 , 实验中要求被试对他人(内族人/外族人)的分钱提议作出决策, 记录被试的行为反应与实时生理指标 ,考察族际偏向情境下的情境动力特征及其社会心理功能。将以上子研究的数据联合后分析其族际冲突心理预警指标价值。研究 4根据前面的族际冲突心理预警指标的研究结果 , 基于突变级数法建构族际冲突心理预警系统的指标结构及族际冲突心理预警系统层级突变模型 ; 采集新样本数据进行模拟和效度检验 , 利用脆性理论考察模型的实用性。旨在建构并检验族际冲突的心理预警模型。
3.4社会决策的衍变
就社会决策而言 , 尽管李纾、李红与刘永芳等人做了开拓性研究 , 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部分仍然沿袭了西方 “自我本位 ”的文化预设。事实上, 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崇尚的是 “他人本位 ”, 例如中国家庭从小就以 “孔融让梨 ”的故事为例教育要学会谦让 , 首先想到的是他人 (包括平位阶层的兄弟姐妹、上位的长辈以及下位的子女等等 ),然后是自己。这才是中国人进行社会决策时的典型模式 , 即人际互动的开放式社会决策。也就是说, 决策者受他人影响。因此, 我们对中国人社会决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社会的基础之上 , 才能构建属于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决策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 当中国人面临决策时, 同样体现了“差序”观。一方面首先对他人进行身份识别 , 在此基础上启动了对他人所属群体的期望。与此同时, 主体也激活了自我认知 , 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产生一定的心理距离 , 即因自我与他人社会归属的差异造成的心理落差 , 对此我们称为 “社会距离”。这种社会距离决定着人际互动和社会决策的模式。另一方面 , 主体完成对群体、人际与自我之间的评估之际 , 还需考虑外周的名利因素。通过对名利得失的权衡 , 最终做出决策。同样, 名利对于东西方人来说意义迥然。在西方人看来 , 人人平等 , 谁都有权利追求利益得失的最大化。但是中国却不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观中 , 人们面对得失, 所做的决策往往表现为舍利取义 ; 其抉择的标准则是责任与荣誉高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会决策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 , 而是为了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甚至是所属群体 (如家庭、家族、乡里等 )的社会地位。例如从大事上来说 , 当世界上一些国家与地区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国人民毅然伸出了援手纷纷从物质上、精神上支援灾区群众 , 这体现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从生活小事上来说 , 杭州最美丽的妈妈看到小女孩坠楼的那一霎那毅然伸出了双手把孩子牢牢抱在怀中 , 孩子得救了 , 自己却受了重伤。因此 , 这两方面综合体现在中国人的人际互动式决策中 , 即自我、人际与群际间的关系产生了 “自我—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 在此基础上考虑相应的名利得失 , 最终作出决策。研究构思如下:
研究 4:中国人社会决策的基本特征:他位观视角下的“名.利”权衡
子研究 1:中国人的社会决策与名利观的关系初探
本研究通过访谈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 , 形成名利观问卷 ; 在此基础上收集社会决策情境下名利两难故事并标准化, 为后期的实验编制材料。
子研究 2:社会决策情境下的名利驱动研究
本研究采用两难故事决策任务 , 通过 3个实验探讨名利驱动 (名誉/利益)、社会阶层 (即故事主角所处的社会阶层 , 较高/中间/较低)与社会关系 (即故事角色间的社会心理距离 , 熟人/陌生人)对中国人社会决策的影响。实验 1以任务驱动性质为自变量 , 记录被试作出决策时的行为与脑活动数据(采用 fMRI技术), 考察名利驱动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实验 2以任务驱动性质与社会阶层为自变量的被试内设计 , 记录被试作出决策时的行为与脑活动指标考察名利驱动、社会阶层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实验 3采用任务驱动性质、社会阶层与社会关系为自变量的被试内设计 , 记录被试的行为与脑活动指标 , 考察名利驱动、社会阶层与社会关系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
子研究 3:社会关系、社会阶层和名利驱动对不同类型社会决策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道德困境任务 , 通过 3个实验考察名利驱动 (名誉/利益)、社会阶层 (较高/中间/较低)与社会关系(熟人/陌生人)对不同类型决策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实验 1以奖赏类型与决策类型为自变量 , 采用被试内设计 , 记录被试的行为与脑活动指标 (采用 fMRI技术), 考察名利驱动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实验 2以奖赏类型、社会阶层与决策类型为自变量 , 采用被试内设计 , 记录被试的行为与脑活动指标 , 考察名利驱动、社会阶层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实验 3采用奖赏类型、社会阶层、社会关系与决策类型为自变量的被试内设计 , 记录被试的行为与脑活动数据 , 考察名利驱动、社会阶层与社会关系对社会决策的影响机制。
总体来说, 中国人社会认知研究范畴与西方社会认知研究范畴相似 , 即包括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与社会决策四个方面。但是 , 西方社会认知的研究是在 “自我本位认知 ”的视角下展开的, 而我们中国社会认知则应从 “他位认知 ”视角切入。即, 中国人社会认知总的特点是 “他位”认知, 关注人的社会类属。自我认知、人际认知、群际认知这三类社会认知往往交织在一起 , 并且以群际认知作为主线 , 贯穿于社会认知的其他层面, 并最终影响社会决策与社会行为。
综上所述, 本课题组从杜威所主张的“科学与实践相联系、社会与认知相结合 ”的理念出发 , 通过历史与趋势、文化传承与文化变迁、理论与实践的整合 , 力图建构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符合社会认知研究学理、直面当下中国社会心理问题的中国人社会认知理论体系 , 进而有力地解释和预测当代中国人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推动国内社会认知研究的理论探索 ,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认知方法论体系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可以为解决某些重大社会问题、促进教育与公共管理的科学发展以及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
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2013-07-11*
本文获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自我与人际认知的特征:心理与脑科学的整合研究”(12AZD117)资助。通讯作者:王沛, E-mail: wangpei1970@163.com1691
(1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上海200234)(2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心理系,宁波315211) (3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 上海 201815)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