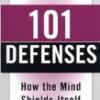:、;
精神避难所为病人提供了一块地方,当与分析师有意义的接触被他体验为威胁的时候,他可以在这里暂避压力,获得相对的平静和保护。不难理解病人有时需要此类暂时的撤退,然而,若是病人习惯性地过度滥用精神避难所,就会产生严重的技术问题。在某些分析中,尤其是在对边缘性或性病人的分析中,病人可能在避难所里一直呆着不出来,这就阻碍了发展和成长的出现。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这种撤退及其导致的与分析师之间的联系中断有很多形式。精神分裂患者的优越感导致的冷淡型,在一个病人身上表现为冷冰冰的降尊纡贵,在另一个人身上则表现为对我的工作冷嘲热讽(mocking dismissal of my work)。有些病人显然是对于做出了反应,他们的撤退似乎表明,分析触及了必须回避的敏感话题。也许,最难处理的撤退形式是那种提供了虚假联系的类型,分析师被邀请参与其中,然而发生联系的方式是肤浅的、不诚实的或反常的。有时候,这些反应可能是由分析师笨拙的或侵犯性的行为导致的,但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很谨慎的分析仍会让病人中断联系。他们会撤退到一个强大的防御系统后面,这个系统就像是一副护甲,或是一个藏身之处,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他们像蜗牛那样小心翼翼地从壳里探出头,可是一旦联系带来痛苦或焦虑,他们就再一次缩回去。
我们已经开始了解,对联系的阻碍与对进步和发展的阻碍是相关的,它们都是由于使用了一种特殊的防御系统而导致的,病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开难以忍受的焦虑。我把这种防御系统称为“的病理性组织(patholog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personality)”,并用这个术语来指代一系列的防御系统,它们的特征是极度顽强的防御,功能是帮助病人避开与他人和现实的联系,从而避免焦虑。对这种方法的探寻让我更细致地去研究各种防御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它们如何互相联系形成复杂的、紧密交织的防御体系。
分析师认为精神撤退是病人卡住、隔绝、失去联系的精神状态,他可能会推断这些状态源自运行了强大的防御体系。病人对撤退的看法可以从他的描述中得到反映,也可以从梦、回忆和日常生活报告所揭示的幻想中得到反映,它们为中病人是如何体验撤退的提供了生动形象的意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象包括房屋、洞穴、堡垒、沙漠绿洲,或类似的看起来相对安全的地点。有时候,意象也可能采取人际的形式,通常是客体或部分客体的组织,能够提供安全保护,例如商业机构、寄宿学校、派别、极权政府或黑社会帮派。残暴或反常的因素常常清晰地出现在描述里,不过有时候组织机构也会被理想化,被赞美。
通常,经过一段时间,(分析师)会观察到不同的代表物,从而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病人防御组织的总体印象。有时候,把这种组织看作是、防御和幻想的组合很有用,它们构成了边缘位相,这与梅莱妮•克莱因(1952)所说的偏执-分裂和位相类似却又不同,稍后我会加以讲解。
撤退提供的慰藉是以隔离、停滞和后退为代价的,一些病人觉得这样的状态令人沮丧,会加以抱怨。然而,另一些病人则颇为顺从地接受这样的状态,感到安慰,有时甚至视为反抗成功,引以为傲,这样一来分析师就不得不去承担由于联系失败而产生的绝望。有时候,避难所被体验为一个残酷无情的地方,病人能够认识到陷入了死胡同,但是更常见的是,避难所被理想化了,呈现为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甚至是理想的天堂。无论是理想化的还是迫害性的,病人都会紧抓不放,认为要好过其它甚至更恶劣的状态,此时的病人确信自己别无选择。对大多数病人来说,他们还是会有所行动的,会谨慎小心地从避难所里探出身来,不过看情形不对的时候就会再退回去。在一些个案中,在病人现身的这段时间,真正的发展是可能发生的,而且病人能够逐渐弱化撤退的倾向。
对另一些人来说,撤退更旷日持久,即便病人确实现身了,取得的进展也是暂时的,病人会出现消极的(负性的)治疗反应,退回到先前的状态中。典型的状况是达到一个平衡,病人使用撤退来避免焦虑,代价是发展几乎完全停滞。如果分析师被作为防御组织的一部分来使用,那么情况就更复杂了,有时候他会毫无觉察地被邀请加入其中,使得分析本身变成了一个避难所。分析师通常会面临很大压力,挫败感可能让他非常绝望,或让他加倍努力想要克服病人顽固的防御,而通常都会无功而返。
对撤退所有程度的依赖在临床上都会出现,一端是完全陷入其中的病人,另一端是暂时性地谨慎使用撤退的病人。撤退的范围和广泛性也会各不相同,有些病人在某些领域可以发展并维持足够好的关系,但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则停滞不前。我在本书中从始至终要强调的观点之一是,即使在卡得最厉害的病人的分析中,变化也有可能发生。如果分析师能够坚持不懈,承受住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那么他和病人就能够逐渐地对这个组织的运作取得一些领悟,逐渐地降低其运作的强度和广度。
撤退的一个特征是,避免与分析师发生联系,同时又是避免与现实发生联系,这在倒错(perverse)的、精神病性和边缘性的病人身上更加清晰可见。避难所于是成为头脑中的某个区域,在这里不必面对现实,在这里幻想和全能感可以不受审查地存在,在这里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这个特征常常让病人觉得避难所非常诱人,通常会涉及反常的或精神病性机制的使用。
在这些卡住的分析中所观察到的防御体系之强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候,它们非常有效地保护了病人免受焦虑的困扰,只要这个体系没有受到挑战,就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其他人则卡在避难所里,明显很痛苦却又不出来,这种痛苦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或带有受虐和成瘾的性质。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病人都因可能发生变化而感觉受到威胁,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回应以更彻底的撤退。
这些情况引发了极大的理论研究兴趣,但是我主要关心的是临床方面,这意味着我首要关注的是组织在个体病人的单个分析时段中怎么运作。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分析师从来都不可能做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因为他总是或多或少地会被拉着去参与的活现。在发展关于病理性组织的观点时,我注意到病人会使用分析师来帮助他建立一个他可以撤退的避难所。我最关心的一直是,循着治疗时段里细微的变化来描述病人如何从避难所里启动现身,却又在遇到无法忍受或不愿忍受的焦虑时再次撤退。
是这个过程那种高度的组织性令我惊奇,让我用“病理性组织”这个术语来描述防御的内部构造。临床图景本身已经逐渐为大多数正在工作的分析师所熟悉,而且已经被很多作者以不同的术语加以描述,稍后我将在本书中回顾他们的作品。亚伯拉罕(1919,1924)对阻抗的研究以及瑞克(Reich,1933)关于“性格魅力”的作品是早期的例子。Riviere(1936)提到过高度组织的防御体系,Rosenfeld(1964,1971a)描述了破坏性自恋的运作。西格尔(1972)、O’Shaughnessy(1981)、Riesenberg-Malcolm(1981)和Joseph(1982,1983)也都描写过陷入强大的防御系统的病人。本书以及类似的作品关心的是那些陷入极端情况的病人,这些情况被认为与在《有止尽的分析和无止尽的分析》(1937)中提到的对于改变的终极阻碍有关。弗洛伊德将这些对于改变的最深层阻碍与死本能的运作联系起来,而在我看来,病理性组织在处理原始破坏性这一普遍性问题上起着特殊的作用。这一问题对个体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它来自外部还是内部。环境中存在着暴力或忽视的性经历导致了暴力、干扰性客体的内化,同时他们又充当了投射个体自身破坏性的合适容器。
无需去解决关于死本能的争议,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在个体的性格中具有某种致命的破坏性,如果不能得到足够的涵容,就会威胁到他的完整性。在我看来,防御组织对所有来源的原始破坏性都起到了约束、中和以及控制的作用,是所有个体防御构造的一个普遍性特征。此外,在有些病人身上,与破坏性有关的问题格外突出,这种组织就会控制整个心灵,而且正是这些个案总是很愿意这种组织开启运作模式。一旦对此有了了解,那么性和正常个体身上类似的、可能不那么令人困扰的版本就很容易辨认了。
这些应对破坏性的方法是否真的成功过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通常观察到的组织倾向于起到某种妥协的作用,既是对破坏性的防御,同时也是破坏性的表达。由于这种妥协性,它们总是病理性的,尽管它们可能是为了适应性的目的,能够提供一块可供喘息和获得暂时性保护的地方。病理性组织使个性失色,妨碍与现实的联系,必定会干扰成长和发展。在正常个体身上,当焦虑超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这种组织就会上阵;当危机过去,它们就会撤回。不过,它们仍旧潜存在那里,如果分析工作触及到可能难以忍受的议题,它们随时可以让病人脱离联系,让分析出现停滞。对那些更受困扰的病人来说,它们会掌控整个人格,病人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左右。
拜昂(1957)对精神病性和非精神病性人格所做的区分有助于将严重受困的病人身上表现出的组织类型与神经症性和正常病人身上存在的组织类型区别开来,这将在第六章里进行讨论,并对精神病性组织进行描述。对于精神病性和边缘性病人来说,这个组织掌控了整个人格,被用来缝补自我受损的部分,结果成为人格的精神病性部分无法或缺的东西。非精神病性人格不太可能对自己的心灵实施破坏性攻击,由于情况不那么绝望,因此投射或内摄的选择就更具流动性。尽管有这些不同,但是不同类型的病人人格的病理性组织仍有很多共同点,当病人有压力的时候就会跳出来。如果分析工作试图帮助病人处理超出他能力限度的问题,那么即便是那些通常功能良好的病人也会陷入困难境地,在这些情况下,病人很可能会使用在正常情况下他很少使用的避难所。
即使在神经症性和正常病人身上,避难所通常以自然而然出现的、或由环境提供的场所来呈现,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是强大的防御体系运作的结果。偶尔,病人自己会认识到他们是如何创建了避难所,甚至可以看清它是如何被作为防御来使用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用防御进行的描述都代表了分析师的观点,是分析师理论方法的组成部分。我发现,对移情中出现的客体关系进行仔细审查特别有助于揭示病理性组织运作的基本原理。要理解它们的构造细节,就有必要知道一些原始的运作情况,特别是,这是现代克莱因的核心概念。这些稍后将在本书中进行讨论,此时只要知道投射性认同会导致一种自恋型的客体关系就足矣,这种客体关系类似于弗洛伊德在关于莱奥纳多(1910)的论文中所做的描述。投射性认同最直接的类型就是,自体的一部分被分割出来,投射进客体中,被认作是客体的一部分,它属于自体这个事实则被否认。由此导致的客体关系就不是与一个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与投射进另一个人中的自体(就好像它是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神话人物那耳喀索斯所处的位置,他爱上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却没想到那就是他自己。对莱奥纳多来说也是这样,他把期的自体投射在他的学徒身上,用他希望妈妈照顾他的方式来照顾他们。
建立在投射性认同基础上的自恋型客体关系肯定是病理性组织的重要方面,但是还不足以解释这些组织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和对变化的阻抗。而且,投射性认同本身并不是一种病理性组织,实际上,它是所有性交流的基础。我们投射进他人中,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感受,不能这么做或不愿这么做都会深切地影响客体关系。然而,对于正常的心理功能来说,能够灵活地、可逆转地使用投射性认同非常重要,由此才能够收回投射,坚定地站在我们的自我认同基础上去观察他人,与他人互动。
在很多病理性状态中,可逆性受到阻碍,病人无法收回通过投射性认同失去的部分自体,从而与自身的某些人格层面失去联系,这些层面就永久性地留存在客体身上,并与客体认同。所有特质,例如智力、温暖、阳刚、侵略等等,都可以以这种方式被投射出去,与自身脱离关系,当可逆性被阻断时,自我就会发生损耗,不再能够进入自体失落的部分。与此同时,由于被赋予了自体分离和否认的部分,客体就被扭曲了。
本书报告的对病理性组织的研究引导我假定存在更复杂的结构。刚刚描画出来的那种防御状况可能是正常分裂的结果,客体或被看作好的,或被看作坏的,而个体努力要从好客体那里得到保护,从而不受坏客体的迫害。正像克莱因(1952)自己所强调的那样,这种客体的分裂总是伴随着自我的分裂,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自体好的部分与好客体有关系,而坏的部分与坏客体有关,二者互相独立。如果分裂得以成功维持,好的和坏的之间就彻底独立,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互动;但是,如果它威胁要瓦解,个体可能会试图通过寻求好客体和自体好的部分的保护来对抗坏客体和自体坏的部分,从而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维持平衡的方法不奏效,那么(个体)可能就会采取更激烈的方法。
例如,可能发生病理性分裂,自体的碎片和客体的碎片以一种更暴力更原始的投射性认同形式被驱逐出去(Bion,1957)。病理性组织由此形成来收集碎片,结果可能再次给人以保护性好客体与坏客体相分离的印象。然而,现在貌似是好和坏直接的分裂,实际上却是人格被分裂成几个元素后每个都投射进客体,然后以客体涵容功能的模拟方式重组的结果。病理性组织可能会以好客体的形式呈现,保护个体不受破坏性攻击的侵害,但事实上它的结构是由从自体和被投射的客体中产生的好元素和坏元素共同组成的,这些元素被当作砖瓦用来建造由此产生的极度复杂的组织。在我看来,被组织主宰的依赖性自体可能也很复杂,并不像起初看起来那么无辜。需要被理解的不仅是建造组织的砖瓦,还有它们的组合方式,因为自体的依赖部分以及分析师都有可能被抓住,陷入维持系统完整的残酷专制的客体关系中。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会尽力说清楚,在人格的病理性组织里,投射性认同不仅限于单一的客体,而是会使用一群客体,客体之间彼此联系。这些客体,通常是部分客体,可能来自病人与早期环境中的人打交道的经验。病人内部世界中了不起的人物有时是基于现实中与坏客体打交道的经验构建出来的,有时候代表了对早期经历的歪曲和篡改。病人经历的创伤和剥夺对人格的病理性组织的创建有着深远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无法了解到底有多少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参与其中。在分析的此时此地逐渐清晰可见的是,这些客体——无论选自环境中业已存在的人物还是个体创造的人物——都是为了特殊的防御目的而使用的,特别是为了要约束人格中的破坏性元素。
我的观点是,人格的病理性组织的重要功能是涵容、中和这些原始的破坏性冲动,为了处理这些冲动,病人才选择了破坏性客体,这样他就可以把自体的破坏性部分投射进客体。就像Rosenfeld(1971a)、Meltzer(1968)以及其他人曾描述的那样,这些客体常常会组成“帮派”,通过残酷和暴力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些结构强大的群体在病人的内心世界里无意识地呈现,并以人际形式的避难所出现在梦里。只要病人不威胁帮派的统治,这个群体就会提供一块安全区域,保护病人不受迫害,不受内疚的困扰。这些运作的结果是要创建一个复杂的客体关系网,每个客体都包含有自体分裂的部分,整个群体以特殊组织所特有的复杂方式结合在一起。组织“涵容”了焦虑,以保护者的面目自居,但是它这么做的方式很反常,不同于我们在正常的涵容中所看到的,比如,比昂所描述的正常妈妈和宝宝之间发生的那样(Bion,1962a,1963)。
这种简单叙述说明了组织能够被拟人化的程度。这部分是由于它发展形成于婴儿早期,那时候很多自然的方面被孩子体验为人的行动的结果;部分是由于内部世界一直住满了客体,客体之间互相关联同时又与主体发生联系。除非避难所得到它所属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保护,否则它就是不安全的。有时候可以获知某些深层的幻想,在其中精神避难所是以客体或部分客体内部的空间显现的。可能会出现的幻想包括:躲避到母亲的子宫、肛门或乳房中,有时候这些地方会被体验为有吸引力但是不许涉足的地方。
这种结构导致的一个主要后果是,个体很难冒险去对抗这些客体,否决他们的方式和目标。结果就是,投射性认同的可逆性受到干扰。稍后我将主张,这种可逆性是通过对哀悼的成功修通建立起来的。重新获得自体在投射性认同中失落的部分,这个过程涉及面对什么属于客体及什么属于自体的现实,而且显然要通过经历丧失来达成。是在哀悼的过程中,自体失落的部分才能重新获得,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做很多修通工作。因此,对客体真正的内化只有在它退回为外部的客体时才能达成,那时它才可以作为独立于自体的人被内化,而且在这种状态下,(个体)才可以用一种灵活的、可逆的方式对它进行认同。象征功能的发展对这个过程有帮助,使个体可以与客体的某些方面认同,而不必与其全部实体认同。
当涵容是由客体组织而不是单一客体提供时,投射性认同就很难被逆转。单独与任何一个客体分离、哀悼它并在这个过程中收回投射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与组织里的其他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通常会被冷酷无情地加以维持来保护组织的完整性。事实上,单个客体之间常常被体验为彼此密不可分,涵容是由一群客体提供的,但这一群人被当作一个客体——即,组织——来对待。
要从其中一个客体身上收回投射,意味着必须面对这种特殊的客体关系领域的现实,而且什么属于客体及什么属于自体必须被区分开来,这样投射才能被剥离并返回自体。即使在防御单独运作的情况下这也是很困难的,而当此客体关系只是复杂组织的一部分时,互相交织的关系网会使这个难度登峰造极。病人于是感到被一个全能的组织控制,根本无法逃脱。如果分析师觉察到这种全能感,他就不太可能想要直接去跟这个组织对抗或战斗。在我看来,这种觉察可以帮助分析师和病人与这种全能感相处,既不向它屈服,也不猛烈地对抗它。如果能够承认这是组成病人内部现实的一个生命事实,那么可能渐渐地就会对它有更好的理解,从而可以降低它对人格的掌控程度。
我已经强调了人格的病理性组织是如何导致分析停滞,导致病人卡住的,他可能会极力躲避接触,从而使分析师很难与他建立联系。在其他病人身上,类似的整体情况与其说是由缺少接触、缺少变化和缺少发展导致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任何确实发生的进展都会很快倒退,有时甚至会全部退回去。一旦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即使是在表面上卡得最死的病人身上,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更细微的变化依稀可辨。因此就有可能做出更详细的描述,这意味着在病人做出尝试性的、有时几乎难以觉察的联络分析师的举动、然而面临焦虑会再次退回去时跟随病人。当病人开始从组织提供的保护中探出头来时,避难所具有的那种随时都可以在其中缓解焦虑和痛苦的特点使得撤退成为一种很方便的选择,有时候联系的体验令病人恐惧,他马上就会撤退。尽管如此,如果这个联系的时刻能被分析师捕获到并加以解释,病人有时候可以对自己害怕联系有所领悟,感觉得到了分析师的支持,从而可能会逐渐扩大他忍受这种恐惧的能力。
如果病人觉得分析师理解当他从避难所里探出头时所面对的焦虑的性质,他就更有可能感觉被支持,并由此进一步摆脱对人格的病理性组织的依赖。在此,克莱因(1946,1952)所说的偏执-分裂位相病人所面对的焦虑与抑郁位相的病人存在重大差别,而对于这两类焦虑的影响,人格的病理性组织都可以提供保护(Steiner,1979,1987)。这个观点提示我们,重要的是不仅要描述在每个特殊时刻运行的心理机制,还要讨论它们的作用;也就是说,不仅是发生了什么,而且是为什么发生——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要努力理解如果从避难所里出来,病人害怕的结果是什么。如果微小的变化被关注,那么当病人从避难所出来而感受到焦虑时,就能够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短暂地略微“品尝”一下焦虑的滋味并记住这种滋味,而分析师可以在观察到它时予以解释。这就使得防御的功能可以被识别,被探查。一些病人依赖这种组织保护他们不受分裂状态和迫害的困扰,他们害怕一旦从避难所出来,极度的焦虑就会淹没他们。其他病人发展出了更大程度的完整性,但是不能面对随着与内外部现实联系的增加而来的抑郁之苦和内疚之感。在两种情况下,现身与分析师发生联系都可能导致(病人)迅速退回避难所,试图重获先前保持的平衡。
梅莱妮•克莱因(1952)从防御组合、焦虑及其它模式的角度描述了偏执-分裂位相和抑郁位相,每种位相都带着各自典型的心理结构和典型的客体关系(包括内部和外部)特征。是在与这些位相的关系中,病理性组织才最容易被理解,实际上,避难所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位相,有着自己的焦虑组合、自己的防御模式,自己典型的客体关系和特征性的结构。我之前用过“边缘位相”这个说法,因为它位于两种基本位相的交界处。
这些位相的命名可能令人困惑,因为我们会自动将它们与特定的临床障碍相联系。克莱因不得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偏执-分裂位相都不意味着偏执型精神病;抑郁位相也不意味着。同样,“边缘位相”这个术语也不能与边缘性病人挂钩,尽管精神撤退这种现象确实很容易在边缘状态中出现,但它们也是精神病性病人的一个突出特征,这是一端;另一端是处在压力状态下的正常个体以及神经症个体。克莱因本人偶尔会提到躁狂位相和强迫位相(,1946),这些更有组织的防御状态与精神撤退有很多共同特征。显然,两种基本位相和边缘位相都会出现在所有病人身上,位相的概念可以帮助分析师思考病人在某个特殊时点上所处的位置。
病人可以撤退到边缘位相上的避难所里,病理性组织保护他不受任何一种基本位相的困扰。本书后面会对这个主题详细论述,使用一个三角平衡图来说明当病人从避难所里出来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要面对来自两种基本位相之一的焦虑。
撤退
(边缘位相)
偏执-分裂位相 抑郁位相
当分析卡住时,在这种平衡中,极少发生可以辨识的变化,病人稳居于由病理性组织提供保护的避难所里,极少会现身面对抑郁或偏执-分裂位相的焦虑。而在卡得不那么厉害时——这当然也可能发生在病人病得很厉害、甚至是精神病人的情况下,则可以辨识出更多变化,转变会发生,(病人)至少可以短暂地面对焦虑。平衡的丧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焦虑或即刻返回避难所的行为,但是也可能会促使分析出现进展。
从人格的病理性组织的一些案例中,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病人甚至会在有了一些发展之后,对病理性组织的需要似乎不再确定无疑的情况下,依然依附于组织。就好像病人已经习惯于这种撤退的状态,甚至是成瘾性的,并从中获得一种反常的满足感。病人与现实相联系的部分常常被威逼利诱离开(现实),整个组织通过在各个成员间建立反常的链接来维持自身的完整。事实上,反常机制在病理性组织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粘合组织和稳固它的结构方面。
避难所特有的与现实之间的特殊关系在阻止(病人)朝向抑郁位相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只有运动到抑郁位相,发展才有可能发生。弗洛伊德,在对恋物癖的讨论中(1927),描述了病人如何采取了一种既不完全接受现实又不完全否定现实的姿态,因而同时持有互相对立的观点,然后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调和。在我看来,反常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这种与现实的关系中得到体现。这在性反常(性变态)中很重要,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基本的“生命事实”,例如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同时被接受和被否认;然而,这其实对任何难以接受的现实层面都是广泛适用的。特别是在面对衰老和死亡的现实这个困难任务时更为突出,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常常采取一种类似的反常姿态。反常的假性接受现实是避难所对病人很有吸引力的一个因素,他可以与现实保持足够的联系来表现得很“正常”,同时又回避了它最痛苦的方面。
当构成组织的客体关系被检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反常的方面。将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联系通常是受虐施虐性质的,包含残酷的暴政,客体和病人自身都被用无情的方式控制和欺压。有时候虐待非常明显,但是暴政通常会被理想化,发展成为对病人诱惑性的控制,病人似乎对此成瘾,常常在过程中获得一种受虐的满足。
只有经过漫长痛苦的工作,病人才会开始感觉有能力对反常有吸引力的拉扯说“不”,因为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其它帮助。然后他可能会觉得不那么容易受到组织的诱骗,而只需要在有特殊压力的时候才去寻求它的保护。随着成瘾的属性减轻,他能够进一步解放自己,面对心灵的现实。一旦这变得可能,哪怕只是部分如此,哀悼和丧失就能导致部分自体的复原,对病理性组织的依赖就会进一步松开。不过,它一直都会是人格的一部分,当现实变得难以忍受时,病人还可以撤退到那里。如果能够如其所是地承认它,也就是说,就是那么一块反常的关系和反常的思维得到认可的地方,那么病人可能就会接纳自己偶尔需要采取这些方法,而无需理想化它们。于是,避难所的保护就可以被看作是提供暂时避开焦虑的休息,但却无法提供真正的安全和发展的机会。就像内心世界的其它元素一样,它也可以被更实际地看待,病人可以最终接受它。
这个初步的框架在随后的章节里会得到扩展。很明显,精神撤退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进行概念化。首先,可以从空间上看作是病人撤退到的一块安全区域;其次,可以看出这块区域依赖人格的病理性组织的运作。组织自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防御体系,还是一个紧密组织的客体关系网。将避难所与偏执-分裂和抑郁位相联系起来也很有用,它可以被看作起到了第三个位相的作用,病人可以从前两个位相带来的焦虑中撤退到这里。最后,避难所的反常性质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病人与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施虐与受虐型客体关系。
陷在精神避难所中的病人给分析师提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技术难题。他不得不挣扎着应对失去联系的病人和似乎很长时间都毫无进展的分析。此外,分析师还不得不一方面与他自己可能陷入与组织共谋的境地而斗争,一方面与他可能撤退到自己的防御避难所而斗争。如果分析师可以对这些进程有更好的理解,他就更能够认清病人的情况,且在病人确实现身的那些时刻是可用的,从而让联系成为可能。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