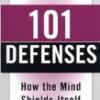本页是内蒙古心理网-内蒙古心理学门户网站最新发布的关于心理学的《划破缄默沉静:芳华期最初的、激动的自我割伤》的详细页面,觉得心理学方面有用就收藏了,重新编辑了一下发到内蒙古心理网-内蒙古心理学门户网站,为了大家阅读方便。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划破沉默:最初的、冲动的割伤
作者:Mary T.Brady
翻译:义 煊
校对:杜净译
来源:心译 公众号
Brady,&Mary,T..(2014).Cutting the silence: initial,impulsive self-cutting in adolescence.Journal of Child Psychotherapy,40(3),287-301. DOI: 10.1080/0075417X.2014.965430
本文探讨了最初的、冲动的自我割伤,并认为早期自我割伤最有可能是在起到交流功能,因为对自我伤害感到最震惊的可能是青少年自己和周围的人。笔者还认为早期的、最初的割伤症状是努力”划开”一直保持沉默的和家庭环境,表明割伤一般意味着涵容和象征化的失败。作者证明了割伤有可能会引起分析师强烈的感受,而分析师可以有与病人的“同调”体验。分析师感受到的部分可能还给病人。两种沟通(即病人的割伤体验和分析师被唤起的感受)的相遇可以创造一个潜在的空间。本文利用临床案例和一个16岁女孩的长期临床材料,阐明割伤通过和师的同调体验,是一种情感上无法表达状态的沟通、涵容和象征的关系。
介绍
在本文中,我重点讨论了青少年最初的、冲动性的自我割伤。我将这种割伤与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仪式化的割伤进行对比,如果最初通过割伤的沟通信息没有被接收,而且促进环境没有以某种方式调整使沟通被接纳,则自我割伤就会成为一种纯粹的排他的和潜在的持久行为。内蒙古专业心理我认为自我割伤意味着涵容(Bion,1962)和象征的失败。
Straker(2006)在她的论文"Signing with a scar"中讨论了更广泛的自我割伤,包括最令人不安的割伤,比如性割伤,在这种割伤中,人"没有直观体验到内心的感觉"(2006: 102),割伤是对自己存在的某种具体的确定。”Favazza(1987)整合了割伤的文化含义,特别是关于成年仪式。Anderson等人将故意自我伤害(DSH)描述为:“……企图使局势保持不变。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无法设想任何有益的变化,人们却试图坚持下去。年轻人经历了一种无力感和对自主的需求,而DSH则表达了这种复杂的现实。虽然这可能会阻止企图,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种“应对"策略,而是年轻人被痛苦困住的一种表现。(Anderson等人,2012年:151)”
我在这里描述的是尚未达到静止的、根深蒂固的且保留着潜在希望的早期割伤。Gardner评论说:“青春期以肉体形式……变化和相关的幻想会导致身体的疏离感--即身体是不同的,是一个客体,是与自我分离的。因此,这是通过割伤进行伤害的做法所涉及的一个关键特征----即身体成为了可以被"处理"或被"惩罚"的东西,因此通过具体的身体攻击而进行间接地控制和处理。”(Gardner,2001年:61)
我同意Gardner的观点,青春期的发展过程会导致身体成为"无法控制的感情和无法控制的本能冲动的目标和接收器"(同上:61)Walsh(2012)在对研究和文献的回顾中评论说,内蒙古心理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关于割伤的流行病学研究。一项针对高中生的全州性实证研究。马萨诸塞州教育部(2004年,2012年)发现,18%的高中生在2003年和2011年都报告了非自杀性(即不想死亡而自我割伤或自我烧伤)。马萨诸塞州13%的中学生在前一年报告了一次非自杀性自伤(马萨诸塞州教育部,2012)。自我割伤行为在女孩中比在男孩中更为普遍;例如,在一项针对加拿大高中生的大型研究中,13.9%的报告自我伤害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二是女孩(Ross和Heath,2002)。自我伤害在青少年中似乎比成人更普遍。Briere和Gil(1998)利用了全国性的抽样,对美国成年人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其中,4%的人报告说至少偶尔有自我伤害行为(与上面提到的18%的马萨诸塞州高中生或13.9%的加拿大高中生相比较)。Walsh报告说,自我伤害者的民族、种族和经济背景范围很广泛,并指出自我伤害的平均发病年龄为12-14岁,可能更容易割伤或掐伤,而男性可能喜欢更有攻击性的方法,如自我击打或打墙"(Laye-Gindhu和Schonert-Reichl,2005,2012:40)。
皮肤容器的破坏
与其他强调了消化的生理过程的自我毁灭行为相比,比如暴饮暴食、催吐、饥饿等,割伤更强调了皮肤的意义。皮肤是早期爱或痛苦的身体/情感接触的场所。皮肤将身体容纳在一起,特别是表现了我们如何被容纳在一起(Anzieu,1989;Bick,1968)内蒙古心理学专业网站。容纳的中断很容易通过皮肤的破裂来表达。
临床案例
'Marcus'是一个13岁的男孩,诊断为症。他的母亲在他8岁时曾自杀未遂,把Marcus吓得不轻。父母都忙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出差。Marcus经常被留在管家或其他家政人员身边。在我们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正在处理对父母失望的痛苦感受,并尝试和我在一起有种家的感觉。母亲刚出国一周,之前的治疗计划取消了。我觉得Marcus很讨人喜欢,情感也很生动。我一直期待着能见到他。随着治疗时间进行,我和Marcus设置了我们可以一起玩的游戏。
M: 我觉得,Kate [他的管家]没有买到我的酸味糖,真是太逊了。她只看了几家店。
T: 你觉得她并没有真的很努力,否则她可以找到你最喜欢的糖果?
M: 是的。
T: 最重要的是,***妈不在,我周五也不在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如果我真的关心你,我就会在这里。(停顿)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能依靠谁。
M: (点点头内蒙古心理网,从膝盖上拉下一块伤疤—他穿着短裤。鲜血顺着他的腿往下涌)。
T: (我感到震惊和惊恐。Marcus要求去卫生间把血迹清理掉,然后回来)。
M: 不结痂的话会不会留疤?
T: 不结痂是不会痊愈的。你不知道该靠谁,而且还伤害了自己。
M: 我并不是想伤害自己,我只是在结痂的时候会这样做。
T: 但我认为,当一个人感到无人照顾,就像他们很难为自己着想一样,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M: (点头。他回头看了看这个互动发生时我们正在进行的游戏) 你有三次赢的机会,我没有任何机会。
T: 我觉得你肯定很关心你能依靠谁。
M: (点头)
T: 但我并不是说你没有任何机会。其中一个机会就是了解这些事情,和我一起思考。
M: 你有iPod吗?我有一些新的音乐,我可以给你播放。我下次会带我的iPod。
临床案例的讨论
此时,我觉得他已经原谅了我说了一些太让他伤心的话,这好像也使他再次对我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有了感受。我得去提供糖果,给他包扎腿。但我也觉得,他已经理解了我说的他的感觉中被忽视然后注定失败。我想,他能够感受到,即使我对他的陪伴有差距,但他也能回想我们在一起的感觉。
Marcus拔掉痂皮的动作非常突然,让人感觉不到他到底是在夸张还是挑衅,也不觉得他是在有地对我表达愤怒。内蒙古心理咨询理论技术马库斯自发地在身体上发起了一个动作,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况下,似乎完全展现了一种没有被父母性皮肤保护且任其流血的感觉。他的动作也传达了一种感觉,即我的评论让他面临无法控制的痛苦。我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与他的状态不同步。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流血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接触到他的体验中未被调解的部分。我对突然涌出的鲜血感到惊恐,同时也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我造成的。他的行为表达了他痛苦的原始性,也唤起了我的体验,那是一种我作为父母而无意中造成他痛苦的体验。Marcus的身体行为传达了—比任何语言都要直接—他强烈未被保护的感觉。
Marcus通过身体展示了内心发生的事情。这一连串的动作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青春期时对肉体进行的行为,什么是象征性的,什么不是象征性的。显然,Marcus的行为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象征,即把感情转化为一种可以思考或梦到的形式。然而,他的行为似乎完美地表现了他的情感状态:原始象征地—同时向象征趋近。这是Marcus表达“还未被思考的东西”的尝试。回想起来,我相信Marcus撕掉膝盖上的痂皮,突破了一种痛苦、抑郁的情绪。虽然这件事让人难过,但却打破了他抑郁状态的隔离。这样的行为表明了身体和精神痛苦的紧密交织。在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了Green(1975)对”象征”一词的原始定义,即“一个被切成两半的物体,当携带它的人能够将两块组合起来时,就承认了它的存在”(Dictionnaires Le Robert)。Green还提到:难道这不是在精神分析设置中发生的吗?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一个象征的两个部分是平等的。因此,即使精神分析工作中分析师作出巨大的努力,在他在脑海中形成一幅病人心理功能的意象,他也会通过观察自己身上的同源过程,提供病人身上所缺少的东西……通过理解沟通的来源和构成之间的关系。但最终真正的分析对象既不在患者一方,也不在分析师这一方,而是在两种沟通的相遇中,在他们之间构成的潜在空间中……一个基本条件是在患者和分析师之间建立同调互补的关系(Green,1975:12)。
和Marcus在一起的时候,这种转化为象征性的东西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努力。他做出了让我震惊的行为,让我接触到他的情感状态。这时,我可以做一件更符合他内心世界的心理工作。我的惊恐与我的病人的惊恐体验是同频的,当他感到过度暴露时,这种过度暴露是由父母带来的和忽视,以及替代照顾者的笨拙努力。他的行动使我更多地停留在负性中。我给他带来了痛苦,且未能充分保护他免受痛苦。可能他撕掉痂皮,既是和自己的沟通,也是和我的沟通。然而,要想真正的感受到情感的意义,这样的行动需要在他人的心目中被看到和了解。Green强调分析师的同调过程,与Bion对、遐想和涵容的交流功能的理解一致。
在理解青少年用身体表达的交流功能,有时"象征的"或"原象征的"这样的词会让人觉得与自我割伤这种出自本能的行为相距甚远。Green的概念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青少年的自我破坏行为需要得到另一个”部分”的满足,才不至于成为空洞的挣扎或潜在的既定防御。当青少年伤害自己的身体时,通过这种有力的刺激,这个行为作为病人“缺少的部分”需要通过分析师的心理工作才能满足理解交流的功能。青少年需要通过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来理解情感的意义。如果伤口和切口没有情感意义,青少年就会形成一种越来越机械化的与自己连接的方式:"这是我做的事情"。事实上,当一种身体症状长期存在时,它的情感意义可能越来越少。
虽然不是割伤本身,但上述事件似乎接近于某种自我割伤,可能都是一种最初的冲动与矛盾的交流形式。割伤,就像身体上的任何动作一样,可以变得仪式化,在某一时刻,不像是一种的为了沟通做出次的努力,而更像是一种容纳自己不要破碎的方式。割伤有可能引发象征意义,但其前提是Green(1975)对两个部分共同发展的阐释。
Lemma(2010)评论说,不应假定改变身体是病态的。她指出,关于身体的行为可以成为学习的来源—例如"什么才像我?"--而不是强迫性动作,即不允许思考和感受。尤其是青少年,他们通过行为来学习。我同意Lemma的观点,不能从外部判断症状,必须考虑内部含义--如创造性或破坏性的因素。我想补充的是,对身体发起的行为被他人情感接纳的方式,与身体行为的意义有很大联系。
自我割伤本身就是对身体发起的一种行为,它既可以用来表达,也可以用来切断情感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改变了心理位置,从情感痛苦到身体专注。因此,割伤可以使其远离混乱的感情,并提供了一个被阐述和被理解的机会。它可以成为对情感问题机械化的反应,疤痕可以成为荣誉的徽章,而不是求助的呐喊。最初的割伤经历也会使主体受到冲击,导致需要与之沟通。在最初时期,自我割伤的青少年经常向别人展示他或她的伤口,通过眼前的紧急情感问题,开始执行象征的另一个”部分”意义。在我的私人执业中,我收到过几个学校辅导员的转介,正在进行自我割伤的青少年朋友找到了他们,或者朋友鼓励正在自我割伤的青少年与辅导员交谈。如果变得更加仪式化的割伤,可能会被认为是因为没有遇到一个能够提供匹配的促进性环境,正如Green所说。主体被留在心理隔离中,独自面对他们的割伤,问题会变得越发根深蒂固。
割伤与被割伤—内部
自我割伤的青少年间接地传达了她与身体的扭曲关系。这些令人不安的症状往往是在青春期发展起来的,因为以前的组织必须转变,青春期的体验有可能使青少年被兴奋和攻击淹没。Anderson (2005)将这种症状描述”潜在地抓住了内部客体关系的两面。”他认为他的青少年患者的割伤行为是无意识地表达了早期对虐待性父母的认同。割伤既可以代表对“客体”的攻击,也可以代表对“虐待客体”的认同。这种概念化是有用的,因为分析师会发现他们努力治疗那些既对自己施加虐待又遭受虐待的病人。不过,在治疗那些几乎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为什么要自我割伤的青少年时,表达这种内在动力可能会让其无法理解。即使是能说出部分故事的患者,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自我破坏的意义。通常,分析者在了解潜在的幻想之前,必须努力解决病人自我伤害的情感体验。
临床案例
“Steven”处于青少年晚期,他在某些方面很聪明,口才也很好,但他很容易爆发疯狂的自我破坏行为:打人、砍人、扔东西、毁东西。这些行为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得最频繁。我觉得自己被他的自我破坏行为所控制。与他在家里的自毁行为相一致,他在某些时候会对我大发雷霆,让我感到压抑,无法思考。在一次这样的咆哮中,我制止了他,并说我认为在他所营造的氛围中,我们无法真正思考。后来他告诉我,他被我说的话打动了。我们最终明白,他的爆发是表达了他小时候的混乱经历,他的母亲是个精神混乱的人并控制着父亲。
临床案例的讨论
我在评论他强烈的情绪体验时,并没有想到这样的解释。有时,在现场阐述情绪起到的作用是,让在自我破坏的无意识意义更接近有意识。Steven意识到,他以为我会像他父亲面对母亲的暴虐一样被动。他对我阻止他的能力的认同,促使他逐渐控制了自己的自我破坏行为。我认为阐明这种无意识的动力是有用的,因为我们之前工作中当我不在的时候,当他感到被抛回他’施受虐’的内部客体关系时,他感到多么无助。虽然此时他的父母已经离婚并且不再被困在一个疯狂的场景中,由于他与父母的疏离程度,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
划开家庭的沉默
经常自我割伤的青少年往往很难将情绪用语言表达出来。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割伤的青少年可能表现为几乎不说话,或者是言语过激,但在其背后却有复杂的情感和家庭环境而一直不被人意识。青少年之所以会采取自我破坏的行动,往往与家庭无法处理核心情绪有关。
临床案例
'Lena',一个16岁的女孩,在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和一个她觉得'恶心'的男孩亲热后,第一次割伤自己。当她开始治疗时,她从“恶心”的联想到了她的父亲。当她说到父母时,她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曾经接触过的一些被收养的孩子,他们觉得父母的负担特别重,幻想着“真正的”孩子会比他们更好。
我对Lena说,她的感受让我想起了一些被收养的孩子。她告诉我,她实际上是被收养的 —— 我与她父母见面时,她父母没有告诉我这个事实。我开始明白,父母非常想把Lena当成自己的孩子,但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空间去让她接受自己是被收养的,包括她对亲生父母的幻想。
当Lena长成青少年后,还是没有为她与收养相关且不断变化的感情留出心理空间。青少年对收养的感觉和幻想可能会因青春期特有的,即性和身份的斗争而有不同的重构。虽然Lena的父母在其职业生活中非常善于表达,但他们一直未能与女儿就其身世进行情感对话。
Lena最初的自我割伤(其中包括对她最好的朋友与一个男孩亲热的刺激、嫉妒和反感的过度体验)导致Lena向这位朋友展示她的割伤。这在上是有道理的,因为她对这个女孩的感觉的确导致了她的自我割伤。后来这位朋友带Lena去找学校的辅导员,正如我所指出的,辅导员介绍她去治疗。Lena的自残似乎"划开"了一种沉默,以她的朋友认真对待她开始。
临床案例
“Avery”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来找我。她割伤了自己,后来告诉了她的一个朋友,朋友又告诉了学校的辅导员。尽管学校给予高度关注,她的母亲似乎想逃避带她来见我。当我终于见到她的母亲,而后又见到这个女孩时,我才知道在这个女孩和她的两个哥哥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因心脏病去世了。这本身就很悲惨,更糟糕是父亲拒绝了治疗,如果当时治疗得当,他的死亡很可能是可以避免的。此外,这个女孩因膝盖先天性畸形而反复接受手术。母亲和女孩一开始似乎都坚持认为她"没事"。在一次与女孩的会谈中,我评论说:“如果一直要感觉自己没事,可能会感觉像穿了一件紧身衣"。她回答说:“手术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使是,我也不知道"。她似乎开始突破最初对家庭痛苦的否定以重新考虑如何看待自己。同时她报告了一个梦,梦中她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场,包括她的父亲。在梦中她是一个青少年--表达了她在重新思考家庭中的意义。不幸的是,在几次见面后,她的母亲就打电话来停止了Avery的治疗,说她"很好"。
临床案例的讨论
情感上的困扰在Avery的家庭里显然是被回避和隔离的。和Lena一样,复杂而动荡的情绪在家庭中不被允许表达。两个家庭都对情绪问题相当否定。割伤似乎是允许表达情绪的意义。Lena的父母会更意识到他们女儿正在挣扎且需要更多的家庭沟通。
割伤意味着家庭和都没有能力去表达情感。Straker写道:“自我割伤根本上是对感受的语言困难"(2006:95)。Lena的家庭逐渐挣扎着允许令人不安的感情出现。Avery的母亲结束了治疗过程,也可能是结束了她去了解女儿在自我割伤中传达的信息的过程。
沉默的累积
当割伤被确定为一种症状时,它就成为处理情绪的一种替代途径。因此,青少年(以及家庭)最初对情感无法表达,可能会促使身体发展一种症状性行为。对症状的依赖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发展不足,因为情感体验一直被回避。
Straker观察发现,虽然关于利用身体来表达“未曾言说的痛苦“和“不可控的情感“的文章很多,但“关于为什么通过身体进行沟通会被认为比通过语言进行沟通更成功,以及在使用语言表达感情时到底缺少了什么”的文章较少(2006:95)。她引用她的一个研究对象的话说:“(说话)需要时间。说话是非常有威胁的,非常不舒服的。好像即使我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Straker认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困难不在于使用语言本身,而反映出用语言去反应生活经验和创造心灵状态的缺失,是涵容情感和影响他人能力的缺失"。与发展主义者观点一样,Straker认为语言的习得既是一种成就,也是一种损失。小孩子用整个身体表达自己的感觉并让位语言的特权——尽管语言本身也可以传达躯体的特质,如语言可以感觉到像一种爱抚或拍打。
临床案例
Dawn Smith博士是旧金山的心理学家,他贡献了以下的临床材料,它可以让人看到割伤—— 一种情感上无法表达的状态——和沟通之间的联系,这种沟通是通过分析师的感受进行的,且最终可以回到病人身上,让灾难性的情感和身体伤害开始被思考和象征。以下临床描述由Smith博士撰写。
Elissa是一名16岁的白人女孩,目前在一所公立高中读11年级。她与父母和她10岁的弟弟一起生活。Elissa 的出生过程很顺利,她按时达到了大部分的发育指标。父母都认为Elissa 一直是个爱挑战的孩子,并开玩笑说她学会的第一个字可能是"不!"。母亲认为她比其他孩子更敏感,这种敏感在 Elissa 处于新环境与新的人相处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学前班,她比其他孩子更爱哭、更爱叫,尤其是在刚开始与父母分离的时更是严重。虽然她适应新的环境有困难,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她就能和别人接触和玩耍。她对食物和衣服的质地总是有些敏感,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偏好,而不是问题。
Elissa 在学校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在经历了学前教育的坎坷之后,Elissa在最初几年还能很好地适应学校的生活,但在她9岁时,她开始在社交方面出现问题。父母说她似乎与班上其他女孩”不同”,她被排除在主流群体之外,没有亲密的朋友。她的父母看到她对这种排斥感到很难过,她与同龄人格格不入。他们形容她“超出了自己的年龄,更像是一个对音乐、书籍和流行文化有兴趣的青少年”。她告诉父母,她觉得自己不合群,但也不是真的想合群。她觉得其他女孩都比较"傻"或"笨",她不想尝试和她们更相似。她的父母担心她在这种条件下会变得抑郁,在她的要求下,最终将她转到了另一所学校。其实这些社会经历对Elissa 来说是一种创伤--一种隐秘的、她觉得她无法告诉任何人的被霸凌体验。她的父母现在认为这里有故意的排挤,但由于其微妙性,很难去做点什么。
Elissa转到了另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似乎更适合她--起初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与众不同"。虽然她交了几个好朋友,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同龄人可以交往,她也看起来很沮丧。她的父母希望升入高中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改变,但这比他们预期的要困难得多。和以前一样,虽然她交到了几个朋友,但她并没有感觉到和他们很亲近,她感到孤立无援,心情烦躁,情绪低落。就在这时,她的父母第一次为Elissa 寻求治疗。
Elissa 在14 岁时曾接受短暂的治疗,父母都认为这次治疗并不成功。Elissa不断地告诉父母,她讨厌去治疗,认为治疗没有帮助,并拒绝与治疗师交谈。当她拒绝再去时,父母终于终止了治疗,因为她拒绝说话,父母觉得强迫她没有用。一年后,她的父母联系了我。他们担心她更加消沉和无望,在学校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这时,她开始逃课,不交作业,还和几个老师吵架。她告诉父母,自己感觉"很糟糕",并同意试着再去参加治疗。
父母形容他们彼此的教养方式大相径庭,父亲比较严格,喜欢设定界限,但不喜欢谈论感情。而母亲则难以设定界限,但觉得自己与女儿的关系很密切。
我已经为Elissa 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每周一次的治疗。在她开始治疗的几个月后,她的父母发现她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自残。不清楚她自我割伤有多久了,也不清楚频率有多高,因为 Elissa 拒绝谈论这个问题。在家里,父母会试图和她谈谈自我割伤问题,但这总是以Elissa变得歇斯底里而告终--哭泣、尖叫和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她的自我割伤行为让父母极其。
有时,她的父母和我都在想,要不要给Elissa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症。我建议进行神经心理学评估来澄清这个问题,父母一直不愿意进行评估,他们觉得女儿可能不会配合。阿斯伯格症候群的诊断将理解为Elissa是把对人的困惑和一种被外界刺激攻击的感受匹配起来了。我一直在帮助她的父母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 Elissa - 接受真正存在的女儿,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女儿。他们对这种转变持开放态度,并为之松了一口气,他们在养育孩子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Elissa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不愿意配合的病人。情况好的时候,当一些沟通是可能的,她会告诉我,她不想来治疗,谈话永远不会有帮助,和我见面是浪费时间。她没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这不关我的事,她讨厌学校--学校里的人和其他人。问题很烦,并且吓到她了,她也很少回答。有一次,当我问起她在网上看到的一些事情时,她告诉我"那些信息对我来说太过强烈了"和"我最好别知道"。
其他时候我们双方的沟通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她根本不说话,拒绝我与她接触的所有尝试。她的父母越是鼓励她向我诉说她的抑郁和自我割伤,情况就越是糟糕。
第一次真正的有突破发生在我建议Elissa可以谈谈她想要的东西时,而不是别人想让她谈的东西。结果,她的话语一泻千里,我都跟不上。Elissa表示,她与人交往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互联网。而互联网上的交流往往是刺耳的、令人困惑的,但让她找到了一群其他被疏远的青少年,得到了一些安慰。如果我不能立刻理解她所表达的意思,她会立刻停止这些分享。Elissa会陷入沉默和绝望来回应我,除非她能被立刻理解到。
以下的见面在许多方面都很典型,但不太典型的是,它是在Elissa可以在见面中更自由地说话的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在这次治疗的前一周,在父母的坚持下,我们举行了一次家庭见面,因为他们感到绝望,担心他们无法理解女儿。这次会面与之前的不同是,之前都是单独的父母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他们转达了他们对女儿缺乏"进步"感到越来越多的挫折感,最近的割伤和越来越多的反抗就证明了这一点。割伤对父母来说一直都是极大的,他们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他们充满了困惑、愤怒和绝望。我体会到这次见面是有成效的,能感到父母们的关爱和担心。Elissa似乎很感动,也很感激他们的参与。他们要求她向他们寻求帮助,而不是自残。
在我和Elissa见面前大约15分钟,我听到办公室外有争吵声。听起來像是一個青少年在对某人大喊大叫,我不知道那是不是Elissa。我开始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我希望那不是她。她走了进来,比平时更加显得皱巴巴的--她根本没有梳理头发,也没有注意自己的外表。
E:(她没有眼神交流,微微耸了耸肩,开始解开耳机)。
T:(我知道这预示着我被拒之门外的开始。)你今天似乎很不高兴。
E:(没反应,把耳机放进去)
T:这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一天。
E:(把她的音乐开得很大,我现在可以通过她的耳机听到,她显然听不到我的声音。)
T: (我开始思考见面前办公室外的尖叫声,不知道她今天为什么这么不高兴。我在想,***妈今天可能带她来了,这往往会让她更暴躁。她的音乐开得很大声,显然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在想这个疗程会有多长,她最终会不会让我和她说话,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注意到十分钟已经过去了,担心接下来的40分钟。当我在等待一个表明我们可以互相说话的信号,或者她会容忍我说话,并试图与她接触时,我知道可能我是为了安慰自己。如果我让她单独呆一会儿,她会给我一些信号或暗示,表明她愿意与我接触。我希望是这样,但今天感觉有些不同。这些暗示诸如把她的音乐声调小一点,进行眼神交流,发出某种声音,或者气呼呼地把耳机拉下来都没有。我又等了十分钟,没有任何可能沟通的迹象)。
T:(大声)看来你是真的不想和我说话了。
E: (没有反应,没有眼神交流,也没有开口。)
T:(我又等了一会儿,感觉有点绝望,因为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看来今天我们说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觉得很失望。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想这是我的防御心理,因为她今天似乎太生气了,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在想上周和她父母的会话,虽然看起来她和父母之间有真正的关怀,而且会话中做的工作也带来了一些更多的理解,她今天的状态可能与此有关)
T: (摆摆手,想引起她的注意。)我们能谈谈吗?
E: (没有回应,没有眼神交流,她转身走得更远。)
T。(我再次等待。只剩下10分钟了,这似乎很糟糕。我挣扎着是要更努力地让她参与还是等待。催促似乎是侵入性的,当她明显处于某种痛苦中时,什么都不做似乎也是不对的。我开始对上周的见面产生更多的疑惑,也许是她之前在我办公室外面的尖叫。也许她害怕回到咨询室。我决定让她在这种状态下离开会更糟糕,我给她写了一张纸条,请她让我和她谈谈)。
E: (生气地拉下她的耳机。)什么?
T: 你今天好像很生气,不知道你今天见到我是不是很不高兴?
E: 不,我告诉我妈我恨你,她在浪费钱,因为我*妈的恨你,我恨来这里,它不会有帮助。
T:和我说话没有帮助。
E: 显然是的。(插上耳塞,转身离开。)
T:(我开始觉得她的状态比较慌乱,因为上周被逼得太紧了。我觉得我和她的父母的见面,某种程度上让她失望了)。
T: 我觉得你今天的状态很糟糕,生气,沮丧。(她打断我的话)
E: 我只是他*的恨你。
T: 我知道,但我觉得你今天更恨我。
E:(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也许吧。
T: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上周让你父母同时来这里,让你陷入了困境。
E:(耸肩)
T:我做的太过了
E: (进行眼神交流,第一次看我。)
T:我们说的那些话,那些感觉,还要表达出来太难,太可怕,太强烈了。
E:(继续进行眼神交流。)
T:(我现在觉得很伤心,觉得自己其实做了一件伤害她、吓到她的事)我做的对你来说太过了,我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
E:(耸耸肩,但继续进行眼神交流。)
T:时间到了。
E: (看起来很惊讶。)好吧,下周见。
临床案例的讨论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在讨论自我割伤的时候提到这一节咨询?毕竟她甚至都没有提到割伤。然而,我想说的是,这几乎没有言语的、充满情感的一小时,正是我们在治疗一个诉诸于自我割伤行动的青少年经常面临的问题。很明显,在这一个小时里,Elissa发现她强烈的愤怒和仇恨难以承受,于是又陷入了混乱的沉默中。她的耳塞和音乐似乎是起到第二层皮肤的功能,把Smith博士排除在外。Smith博士试图与她接触,在咨询即将结束时,Smith 博士感觉因选择侵犯 Elissa 的隐私还是放弃 Elissa 两者之间的困难。她采取了第三种策略,给Elissa一张纸条,询问她是否可以和她谈谈。这个行为开始了真正的开场。虽然Elissa对这字条要求她谈话感到愤怒,但这一点很重要。Elissa 会让到人们感到与她交谈是一种侵犯,是将自己的需求强加于她。这个请求暗示了 Elissa 有权拒绝,也暗示了 Smith 博士想与她交流的愿望。它还传达了Smith博士一种游戏性的灵活,通过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接近Elissa。
Elissa正在与爆炸性的情绪作斗争。而Smith博士在这一小时里也饱受煎熬:她感到无助、无能、无法沟通。Elissa和Smith博士都体验到似乎无法控制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强烈感受。然而,Smith博士可以接受一些无助的感觉,并试图与病人接触。当Smith博士说她的病人比往常更恨她时,我想Elissa开始感到一丝希望,她的极端感受可能会被转化为能被理解的东西。我想她开始感觉到可能可以有层皮肤,它可以让一些东西进来,并将一些东西挡在外面,而不是如大声的音乐和她的对抗这样僵硬的过滤外在的刺激。
Smith博士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她选择与Elissa和她的父母举行,对Elissa来说,可能太过强烈。Smith博士是在表达Elissa可以承受这样的痛苦。父母性和治疗性的功能是衡量孩子在特定时刻处理某事的能力—并帮助涵容和消化。Smith博士为做了一些Elissa还没有准备好的事情而真挚地承担责任,Smith博士回到了真正的分析性和父母性功能。她受到来自Elissa对自己的强烈控诉,她也证明了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处理它。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些挣扎,我们的孩子或病人又如何面对他们的挣扎呢?Smith博士的这次会谈,可能为Elissa最终能够考虑她伤害自己的方式,或者可能开始考虑这种通过伤害自己来伤害她的父母以及Smith博士的方式。
Smith博士接受了仇恨和愤怒。我们不知道如何发生的,但我们开始猜想这与自我割伤行为有关。我们开始感受到仇恨、愤怒和无能—以及对伤害的担忧。也许这次咨询的进展是从仇恨和愤怒走出来,并连接到力量与关切。这一个小时找到了连接彼此的意义,因为Smith博士容忍了无能和无助的体验。我想象Elissa在面对自己的感受时,常常感到无助。Smith博士与Elissa的无助感有了同源的体验,可能特别是在前一次会面,面对家庭三个人的时候。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Elissa很早就是个“困难”的孩子,但她的同伴问题是从青春期早期开始变严重。青春期的变化让Elissa与其他女孩格格不入,那些女孩恰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这也可能让她无法和自己说话,更别提和父母说话了。
对Elissa的一种看法是,在某些时候,她发展出了"第二层皮肤"(Bick,1968: 484)。她感到无法依赖他人或无法涵容情绪,于是她变得伪独立,表现的很攻击。可能是她的父母对她的愤怒做出了回应,但却听不到她的无助。Elissa生活在一个僵硬的、具有攻击性的外壳中,这让她感受不到无助,但也让她难以接受。Smith博士面对Elissa愤怒时表现的坚韧,使她能够给予Elissa情感上的理解。Smith博士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她认为在与Elissa的父母见面时,改变了治疗的设置,虽然动机良好,却让Elissa深感不安。病人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所淹没,又面临着沟通挑战,因此特别容易受到设置变化的影响。
结 论
早期的冲动性自我割伤,主要发挥的是沟通功能,也使青少年和周围的人震惊担忧。自我割伤涉及到涵容和象征的失败,而自我割伤明显与身体的关系可能代表着无意识的内部客体关系问题。理解这些潜在的问题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治疗师经常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情感沟通的青少年,以及一个对情感理解排斥的家庭。
在本文中,我选择突出Green对象征形成的描述:一个伤痕累累或流血的病人坐在你面前,在视觉上唤起了部分沟通或象征的意义—被割伤或不完整的东西。另一部分象征或情感意义需要通过分析师的感受去理解。Green讨论通过分析师的同调体验来完成象征部分的“回归“,有什么东西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被割掉了。当然,Green是在更广泛地谈论象征的形成,但他关于一个客体被切成两半的意象引起了共鸣。Green在精神分析师身上的"同频过程"与Bion关于投射性认同通过母性遐想而转化的概念是一致的。未代谢的β元素可以转化为α元素,并返回到儿童/患者身上。Bion认为母性遐想的过程对思考和做梦的能力至关重要。
考虑自我割伤与青少年的其他身体症状,如饮食失调、药物滥用和自杀尝试之间的异同是很有意思的。例如,饮食失调与摄入和排出问题有关,因此需要关注内摄、融合和消化的过程。发展性压力可能导致内外部父母性的涵容客体和更早期的自体的隔绝或疏离。这种疏离会让青少年的感官和情感体验溢出。割伤特有的特征,即缺乏容器、象征和情感表达的特征,也是与其他身体症状共同的要素。显然有些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时,其内在和外在的容器远远低于其他孩子,因此当青春期袭来时,他们特别容易出现身体症状。
在自我割伤中,皮肤显然是重要的。在时期,皮肤是拥抱、感性和爱,同时这些的缺席会带来毁灭性的丧失。自我割伤似乎特别与被容纳的破裂有关。Lena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和一个”恶心”的男孩亲热,产生了崩溃的情绪。她觉得自己和朋友的位置被侵犯了。皮肤也是“与他人交流和建立象征关系的主要手段”;此外,它也是可能会被他人“留下的痕迹的"(Anzieu,1989)。自我割伤涉及到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但这种冲动与被他人伤害的感觉几乎没有区别。割伤和纹身、穿孔一样,都在讲述一个故事(Lemma,2010)。
青春期自我割伤的症状是一种需要”划破沉默”的沟通,需要被他人听到。割伤是一种涵容失败的夸大表达,割伤是青少年通过自己的身体呐喊着这种失败。如果没有被’听到’,那么青少年可能会升级出越来越多的自毁行为,或者最初症状的希望就会僵化成为一种更慢性的既定症状。如果能“听到“皮肤性涵容的失败,就像我相信Smith博士在上面的案例所完成的那样,让青少年开始与一种象征性的叙事所建立联系的可能,而不是被束缚在身体表达上。精神分析的框架也是一种“皮肤”,它代表了一个内部空间,由时间、频率、隐私等结构的“皮肤”所限定。治疗框架的改变,会使病人特别容易感到不被涵容的时候,并通过生理和心理皮肤的破裂来表达。
最后,我引用Frances Tustin的话:.....心理治疗了解人性的暴风雨,并通过关爱转化为现实的面对涵容的需要(Tustin,1984: 288)。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将自我伤害的青少年的那些暴力的、无法抑制的情绪转化为有意义的共同理解。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以上就是《划破缄默沉静:芳华期最初的、激动的自我割伤》的全部内容,涉及到割伤、父母、自我、自己、没有、一个、身体、行为等,看完如果觉得随心理学学习有用请记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