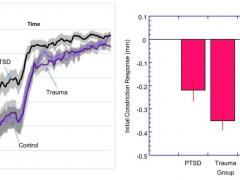我对的体验和反思
文 | 托马斯·科茨
作者:托马斯·科茨(Thomas B Kirsch),美国分析师,生于英国伦敦,其双亲跟随在1930年代在苏黎士从事分析工作。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医学系、国家心理卫生学会顾问、荣格学会旧金山分会理事长、国际分析会理事长及副理事长。
本文是在众多政治和文化力量的背景下,对一系列创伤事件高度个人化的阐述。我的出生创伤发生在欧洲陷入一片混乱的时候,那时希特勒和纳粹正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力量。由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世界局面,当时也有是否应当把我生下来的疑问。我的肾细胞癌以及II型糖尿病的病史同样对我个人造成了创伤,并且让我接触到了不同的文化态度。
创伤是理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弗洛伊德最初构想的癔症理论中,他假定受到了真实的身体引诱。只是到后来他才重构了他的理论,将真实的身体引诱改为了幻想的诱惑。荣格并没有将创伤归纳为他整体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我和一些第一代荣格分析师的长程分析中,创伤的问题很少被提及。事后回想起来,我发现创伤是我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在分析中却从未对其如此描述过。撰写我的回忆录使我重新体验到了一些创伤经历,并且使我到这些经历实际上是多么地具有创伤性。
让我从我的出生开始讲起。我出生时由于胎位不正,是通过臀位分娩生下来的,也就是说我先露出来的是腿。在我出生的1936年,这意味着医生不得不进行胎儿内转,好让我的头先露出来。在转动子宫内胎儿的过程中,胎儿经常会遭到手臂骨折和臂丛神经受伤,这些创伤日后可以治好。这叫做厄尔布麻痹(erb paralysis)。我出生的时候左臂骨折,但是没有神经受伤。在子宫外生活的最初几周,我的左臂上绑着石膏,我被告知我当时看起来像个警察。根据奥托·兰克的著作,这是真正的“出生创伤”。我的家人觉得我那骨折的胳膊“很可爱”,并且我那早期骨折过的胳膊未曾在身体上妨碍过我的活动。我一生都是左撇子。
我的第二次创伤经历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纳粹日夜不停地轰炸伦敦。我们全家人都睡在避难所里,对我而言,那意味着我在一张椅子上睡觉。在屋子里过夜是不安全的。那段经历对我产生了两个长期影响。一个是,在我抵达美国的好几个月后,我都害怕睡在床上,仍然继续只在椅子上睡觉。甚至到现在,当我坐在一个舒服的椅子上时,即使我不累,也还是很容易睡着。第二个长期影响是我对嘈杂噪音的反应,我会把手放在耳朵上去减少噪音。相比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对嘈杂噪音的反应好多了,但是我对突然产生的噪音还是很敏感。
当时我父母认为英格兰会被第三帝国(即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所侵占,因此在1940年10月获得了进入美国的许可。这意味着在德国潜水艇平均每个月击沉350,000吨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横渡北大西洋。我们每天都要演习使用救生艇,好在有鱼雷击中我们的船后逃生。写回忆录时,我的编辑找来了我们当时所乘坐的船的照片。当我第一次见到照片上那艘船时,我泪如雨下,因为我一眼就认出了船的甲板和救生艇,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时。所以,活过了对伦敦的闪电战空袭、还有横渡北大西洋,对我来说都是巨大创伤经历的一部分。当时渡海非常危险,而我们幸运地活了下来。尽管那时我只有四岁多,我仍能感觉到我们处在巨大的危险中。
现在我想描述一下过去三年来我所经历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给我带来的创伤。成人以来,直到2011年12月1日,我的健康都是相对良好的。我从二十多岁起背部就有长期的问题;我还患有痛风,但过去25年来一直都控制得很好。背部问题使我无法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但多年下来情况已经逐渐好转。我尝试过很多整体性医疗的方法,包括中医治疗,这些方法改善了我的背部情况。
在2011年夏天的常规检查中,我的眼科医生诊断出我的左眼有静脉血栓,并建议我预约斯坦福眼科研究所,那里是专门治疗视网膜疾病的高端眼科中心。预约的时间安排在12月1日,从那天开始,我的健康成了一个经常需要担忧的问题。给我做检查的技术员脸上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当然她不会告诉我她看到了什么。在我预约的那天,眼科专家有急诊因此没法见我了。晚上7点钟他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左眼动脉上有胆固醇栓子,这是一种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是从我的内部颈动脉上转移到眼动脉上的。
就像我的情况一样,这种病常常没有症状。但是它意味着血管下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而硬化的斑块分裂开来,并转移到了眼睛上。因为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主要通道,这种病不是一个好迹象。第二天的超声波检查结果发现,我两侧的颈动脉都已经完全阻塞了。我没有中风或死亡的唯一可能就是这种阻塞是逐渐形成的,以至于形成了非常活跃的侧支循环。没有迹象表明我曾有中风。荣格的理论中提到补偿,而这里就是一个我的身体是如何补偿潜在的、致命的情况的典型例子。
由于颈动脉存在着很多种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医生决定检查我全身所有的主要动脉是否存在粥样硬化。对于一个像我这个岁数的男人来说,我其余动脉的状态还不错,但是当他们检查我的主动脉时,发现我的左肾上有团块。这也是没有症状的,但引起了注意。
通过我放射科朋友的努力,我很快地见到了一位泌尿科医生;两个月后,癌症肿瘤被取出,而我被告知不需要进行任何后期治疗。这种病的正式名字叫做肾细胞癌。后续的CT扫描开始显示出我的肺上有斑点。我的医生怀疑这些是从肾上转移过来的小瘤,认为我应该接受后续治疗。所以手术结束六个月后,我被转给一位肾癌专家,从那时起一直接受她的治疗。而直到15年前为止,这种癌症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我的一位挚友以及同事,埃利·亨伯特,他的预后和我差不多,但几年后癌症复发了,最终他死于这种疾病。从那之后开发了一种叫做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药物,能够控制这种疾病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医生用这些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药物中的一种对我进行治疗,接下来大约10个月里,我对药物的反应都很好。然后癌细胞又开始增长。
我的医生参与了一个用新型药物抑制癌细胞增长的全球性研究;这是一种治疗不同癌症的全新方法,因为这些新型药物会增强免疫系统。这种药物会让人体血液中的T细胞专门去杀死会引起几种癌症——包括肾细胞癌——的癌细胞。这种药物使我胸腔的小瘤变小了,肾脏也没有进一步的癌变情况。由于组检查变得更加可负担,根据病人的基因结构采取特殊的药物也变得可行。
然而这种药物并非没有副作用,我患上了自身免疫性肺炎,需要靠强的松(肾上腺皮质激素)来缓解症状。服用强的松就意味着我需要经常进行CT扫描,而且每个月都要去斯坦福大学的泌尿科就诊。在得知自己患有肾脏癌的那天,我是如此震惊,以至于在倒车开出停车场时,我把自己的车跟旁边的车好好地撞了一回。我以为我已经消化了这个消息并且接受了事实,但显然我内心里仍然烦乱不已。现在,我仍然每两周进行一次药物的注射,但之前曾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患有肺炎而停药两个月。
2014年5月,我又经历了一次关于健康的创伤。我与妻子一同前往欧洲,准备在哥本哈根进行专题研讨之后继续赶往柏林举行关于我父亲的演讲,因为德国的荣格分析师们正要在我父亲1927至1933年间作为荣格分析师执业的地方加上纪念铭牌。在动身之前不久,我开始出现尿频,并且经常觉得很渴。我以为我是因为要在柏林为父亲做演讲而感到。我们先到了哥本哈根,我和简为那里的分析师候选人举行了研讨会。第三天早上,我完全没法动了。我感到整个人都筋疲力尽,意识也有些不清。
我被送到了急诊室,不到10分钟我就被诊断为患有酮酸性糖尿病,立刻住了院。我有明显的家族糖尿病病史,但我还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此劫。回想起来,我和简都是完全拒绝考虑这个事实的。我在哥本哈根只住院治疗了4天,就不得不赶往柏林参加纪念铭牌的揭幕仪式。不幸的是,即使到了柏林,我仍然需要住院治疗,于是约尔格和贝亚特·拉舍安排我住进了夏洛特医院,一家有300年历史的著名医院。
在那里,来自洪堡医学院的训练有素的医生们为我进行了极好的治疗。我的血糖指标降了下来,于是他们允许我出院做演讲并且首发荣格与詹姆斯·科什(James Kirsch)书信来往的德文版本。在这里接受了6天的住院治疗后,我们又继续踏上前往苏黎世的旅程。
这次的住院治疗对简而言同样是一次相当大的创伤。夏洛特医院位于一大片紧密相连的大学建筑群当中。简不会说德语,这偌大的校园会让她迷路。她每天从旅馆赶来医院时,都不得不跟出租车纠缠一番以找到我所在的那栋楼。
而对我的创伤则是,住在这么古老的医院里,躺在古老的病床上,望着另一栋我父亲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工作过的老房子。我一辈子都在回避柏林这座城市,而现在我却以一个病人的身份躺在这个没有一个护士会说英文的古老医院里。幸好这里的医生都会说英语。几乎每晚我都会有一个新的室友。当我想象着父母当年在柏林的生活时,我父母一生的经历就不断地涌入我的思维。我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结。过去他们总是努力保护我,也保护他们自己,避而不去柏林,然而现在我却完全身陷于柏林,幻想他们早年在这里的生活。我也邀请了我的儿子来参加纪念铭牌的揭幕仪式,所以当他到了柏林之后,帮了简和我很大的忙。
我所说的这些创伤为什么是文化性的呢?1940年,从英国到美国都是相当具有创伤性的。在洛杉矶,黑人、西班牙人以及白种人被种族隔离开来。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见过任何黑人或西班牙裔的学生。后来我们一家搬进了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居民区,但我仍觉得自己是个难民。在学校,我是唯一不会说美式英语的小孩,我因为自己的英式口音被嘲弄,很快就改了口音。我的父母并不太懂美国的习俗,所以也没有人来指导我的言行举止。杰瑞,比我大9岁的异母哥哥,对美国习俗掌握得更好一些,就常常帮助我母亲应对困境。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每晚都睡在椅子上,并且出现了不少神经症的症状;其中有些症状持续了很长时间,其它一些则很快消失了。
在哥本哈根被诊断出糖尿病、并且在丹麦和德国两地接受治疗是十分有趣的经历。丹麦是社会福利非常好的国家,政府会照顾公民的一切需求。这包括了所有的药物以及医院治疗。甚至作为外国人的我也有资格获得免费的医药服务。丹麦的医院非常干净,而且因为担心我会带入外来的传染病病原体,我是被隔离收治的。护理的质量非常好,但没有任何人来全权负责我的治疗。
另外,因为丹麦采用的评估血糖的方式不同,我很难将其翻译成美国医生使用的、让我轻而易举就能识别的评估方法。再加上当时我病得相当重,思维也不清晰。直到我准备离开时,我才见到了一位糖尿病的专科医生。这位医生尝试让我多住院几天,可是我必须要去柏林参加纪念铭牌的揭幕仪式。我的糖尿病在哥本哈根并未得到充分的治疗。我很感谢哥本哈根的医院给我提供的非常好的照护,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有多少时间是浪费在无人负责治疗的阶段。
在柏林,我是在一家历史悠久、还在使用过时设备的医院里接受的治疗,但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来负责治疗我的病情,他确保我的血糖降了下来,让我能好好地做完演讲,并且顺利回到美国。住院费很少,我愉快地付了医药费。同样的病情,若是在美国的医院里进行治疗的话,要贵50倍以上,尽管在美国,我的医疗保险足以支付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费用。德国的医疗体制是由一位教授领导,另有一帮年轻医生、住院实习医生以及医学院学生们参与会诊。德国老式的专制体系仍然健在。幸运的是,负责我的这位教授认识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这给了我特殊的待遇。起初大部分来自前东德的护士们对我有些冷淡,不过当他们看到教授对我照顾有加时,态度也就有所改变。
我生病的这段小插曲中包含了文化元素。我尝试去描述我在丹麦和德国所受到的治疗的不同。对于我的糖尿病,这两地的治疗都既具有积极的方面,也具有消极的方面。丹麦的医疗体制是人人平等,这意味着我接受的是完全集体化式的治疗方法,而并不考虑我的个人情况。而在德国,我身处于相当冷淡的环境中,一点儿也不舒服,但却接受到了非常好的个性化治疗。这使我能够状态良好地出院,并且回到家中。到了美国,我在斯坦福大学医院接受了治疗,主治医生是一位俄罗斯籍的糖尿病专家,当我的血糖失调时,她总是随传随到。目前,我的血糖状态是自从被诊断为糖尿病以来的最佳状态了。
有趣的是,我的癌症主治医生和糖尿病主治医生都是,并且都来自国外,我的癌症主治医生来自印度,而糖尿病的主治医生来自俄罗斯。她们都是先在本国的医学院完成学业,然后再来到美国继续接受研究生的培训。所以这两位医生都会受到来自世界其它地方行医习惯的影响。
这篇文章是一次尝试,希望在大文化的环境下去描述我所经历的一些个人创伤性体验。
(本文选自《心理分析》期刊2016年第一期,洗心岛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转自微信公众号“心理分析与。)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