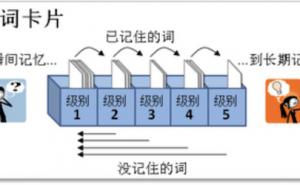的基础 *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济南 250014)
摘要抑郁具有复杂的、非孟德尔式的多基因遗传模式 , 但是目前多数抑郁的遗传研究集中于考察单个候选基因, 不能全面揭示遗传因素的作用机制。近年来 , 多基因遗传得分研究和基因 .基因交互研究分别为抑郁的多基因累加效应和交互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多基因不仅直接影响抑郁 , 还通过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 , 并且这一复杂交互作用存在。抑郁的研究发现多基因可能通过因素、、压力荷尔蒙等间接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未来研究应更加关注多基因与多种环境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抑郁, 探索多基因遗传机制的性别差异, 考察多基因对抑郁影响随年龄的发展动态变化。
关键词 抑郁; 多基因遗传; 内表型; 性别差异分类号 B845
1引言.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根据其表现特征、诊断标准和严重程度的不同,主要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抑郁情绪(depression mood),主要特征是悲伤、苦恼或烦躁等;抑郁综合症(depressive syndromes),除表现出消极情绪外,还伴随着退缩、注意力涣散等行为特征;重性抑郁(major depression)或者抑郁障碍(depressivedisorder), 除上述特征外 ,同时伴有明显的失眠、厌食等躯体症状(Compas,Ey,&Grant,1993;王美萍,张文新,陈欣银,2015)。此外,由于各种情绪失调障碍间具有较高的共发性,抑郁可能还伴随着、恐惧和强迫等不同的症状(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抑郁测评主要包括对抑郁症的筛查和抑郁严重程度的评价。前者是指根据临床诊断标准 (如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V, DSM-V)对个体是否罹患抑郁障碍进行判断,后者是指使用抑郁测评(如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 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Scale, CES-D)对抑郁水平或严重程度(轻度、中度和重度)进行评价(曹丛,陈光辉,王美萍,曹衍淼,张文新,2014)。
在世界范围内,有大约1.2亿人遭受抑郁障碍的困扰。最近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一般人群的抑郁发病率为10%~15%(Lépine & Briley, 2011)。抑郁不仅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失衡、学业失败和社会功能失调(Aronen & Soininen, 2000),而且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Lépine & Briley, 2011)。因此,考察抑郁的致病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至关重要。近年来,伴随着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探索抑郁的遗传作用机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近十几年的候选基因研究主要关注了参与压力反应过程或者影响抑郁神经递质功能的单个基因位点,并不能全面揭示抑郁产生的遗传机制。早期,对白人抑郁患者的家庭谱系研究发现,抑郁的遗传并不遵循亨廷顿舞蹈症似的单基因遗传模式,而是具有非孟德尔式的、多基因遗传基础(Baker, Dorzab, Winokur, & Cadoret, 1972)。近期,分子遗传学和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不仅定位了多种与抑郁密切相关的候选基因(参见综述 Dunn et al., 2011),并且发现多种候选基因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如 Kaufman et al., 2006; Peyrot et al., 2014)。由此,深入探索多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抑郁遗传机制研究的主要趋势。当前研究最为丰富的是5-羟色胺系统基因(如 5-HTTLPR, serotonin transporter-linked polymorphic region, 5-羟色胺转运体关联的多态性位点)、多巴胺系统基因(如 DRD2, dopamine D2 receptor, 多巴胺 D2型受体)及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如 BDNF, brain-derived neurotropic factor,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与抑郁的关联,本文通过梳理这些多基因研究,分析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及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探索多基因对抑郁的作用路径,以期增加对抑郁多基因遗传机制的理解。
2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
通过梳理抑郁的多基因遗传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多种候选基因不仅直接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而且能够调节环境因素与抑郁之间的关联。鉴于此,本文从两个方面归纳分析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一是多基因与抑郁的关联研究,二是多基因与环境因素对抑郁的交互效应研究。
2.1多基因与抑郁的关联研究
早在20世纪70年代,家庭谱系研究已经发现抑郁具有多基因遗传基础(Bakeret al., 1972)。近几十年神经生化、药理学研究进一步揭示 , 抑郁多基因遗传机制的生物基础是影响一种或多种神经递质系统功能的或受体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如有研究发现,5-羟色胺转运体 (serotonin transporters, 5-HTT)功能的抑制可以增加BDNF mRNA表达, 而 BDNF能够激活 5-羟色胺神经元上的 TrkB受体(tropomyosin receptor kinase B, 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 B) (Martinowich & Lu, 2008),进而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 (Hung, Lin, & Huang, 2010)。基于上述生物基础 , 研究者开展了对调控神经递质功能的多种基因与抑郁的关联研究。
2.1.1基因×基因交互效应
基因×基因交互效应可能发生在同一神经递质系统的相关基因之间。譬如 , Felten, Montag, Markett, Walter和 Reuter (2011)以 1041名白种成人为被试, 采用人格问卷 (Affective Neuroscience Personality Scales)测量被试的消极情绪性得分 (包括恐惧、愤怒和悲伤三个维度 ), 考察了同属多巴胺系统的 COMT基因(catechol-O- methyltransferase, 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 )和 DAT1基因(dopamine transporter,多巴胺转运体 )
对个体消极情绪性各维度 (negative emotionality)的交互效应 , 结果发现同时携带 COMT Val/Val基因型和 DAT1 9R/9R基因型的个体报告了较低的悲伤得分 , 而携带其他 3种基因型的个体之间差异不显著。与此类似 , 一项关于孕期抑郁的研究发现 , 在怀孕 36周时, 只有同时携带 MAOA (monoamine oxidase A, 单胺氧化酶 A)低活性等位基因与 COMT Met/Met基因型的女性才表现出抑郁水平的显著升高(Doornbos et al., 2009)。
隶属于不同神经递质系统的基因间亦可能存在交互效应。 Roetker等人(2012)对 4811名白人被试的研究发现多巴胺系统候选基因与神经内分泌系统候选基因交互预测个体是否罹患抑郁障碍 , 并且其交互作用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在男性中 , 同时携带 DRD2 C等位基因与 GNRH1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1, 促性腺素释放激素 1型) T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可能罹患抑郁障碍 ; 而在女性中 , 同时携带 DRD2 TT基因型、 APOC3 (apolipoprotein C-III, 载脂蛋白 C-3) TT基因型和 ACVR2B (activin receptor type-2B, 2B型激活素受体) CC或 TT基因型的个体更可能罹患抑郁障碍。最近, Lekman等(2014)对 1732名重性抑郁患者和 1783名健康成人的研究显示 , 5-羟色胺 2A型受体 (serotonin receptor 2A, 5-HTR2A)基因和 BDNF基因对抑郁存在交互作用的倾向, 同时携带 5-HTR2A A等位基因和 BDNF T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可能罹患重性抑郁。该交互效应得到了有关情绪障碍神经回路可塑性研究的支持 , 譬如 Mattson, Maudsley和 Martin (2004)的研究指出 5-羟色胺(5-HT)受体的活性可以诱导 BDNF基因转录 , 而 BDNF进一步影响与抑郁密切相关的 5-HT神经元轴突的可塑性。
2.1.2 基因.基因累加效应
除了基因×基因的交互效应, 多基因累加效应的研究——多基因遗传得分 (polygenic score, PS)也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根据其筛选基因的途径, 该方法可以划分为两种:候选基因 .多基因遗传得分方法(candidate-PS)和 GWAS.多基因遗传得分方法(GWAS-PS)。
候选基因.多基因遗传得分方法是通过筛选对抑郁具有功能性影响的多种基因位点 (一般是根据科学研究文献选取候选基因 )来计算多基因遗传得分。该多基因遗传得分是通过将个体携带的多种易感等位基因数量 (0, 1, 2)直接进行加和获得的 , 并用作多基因累加遗传指标 , 来预测抑郁症状。采用这种方法 , Pearson-Fuhrhop等(2014)分别以 273名健康成人 (56.8%女性)和 1267名抑郁患者 (58.5%女性)为被试, 考察 5种多巴胺系统候选基因 (COMT、DAT1、DRD1、DRD2和 DRD3)累加得分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 , 结果发现无论是在健康对照组还是在抑郁症患者组 , 个体携带的低活性多巴胺等位基因 (即易感等位基因 )数量越多, 其抑郁水平越高 , 即便在排除了与抑郁关联最密切的单个候选基因 (DRD2)的效应后 , 累加遗传得分的解释率 (9.2%)仍高于任何单基因位点的解释率(低于 7.8%)。
随着 GWAS研究的兴起 , 研究者除了从文献中筛选具有功能性影响的候选基因外 , 也尝试将 GWAS分析得到的、与抑郁存在显著关联的多种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加权求和计算多基因遗传得分 , 即 GWAS-PS方法。该方法通常需要两个样本:首先 , 在探索性样本中进行 GWAS分析, 通过设定基因位点与抑郁关联的显著性阈限 (PT值), 筛选 P值小于阈限的 SNP;其次, 根据探索性研究筛选出的 SNP计算 GWAS.多基因风险得分 , 具体方法是在验证性样本中将被试携带的多种 SNP的易感等位基因数量 (0, 1, 2)按照其预测力大小加权后进行加和 , 用以考察多基因遗传指标能否预测个体的抑郁症状。譬如Demirkan等人(2011)采用该方法, 以GAIN-MDD项目(The Genetic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基因关联信息网络 .重性抑郁障碍全基因组研究 )中的 3540名成人为被试 , 进行探索性 GWAS分析, 筛选出小于 P值阈限的多个 SNP;随后, 对鹿特丹研究序列(Rotterdam Study Cohort)的中年被试 (48.7%女性 )和荷兰吕克芬家庭研究 (Erasmus Rucphen Family Study, ERF)中的老年被试 (58.2%女性)进行验证性研究发现 , GWAS-PS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 , 遗传解释率为 0.7%~1%, 并且多基因得分对抑郁的影响几乎不随年龄发生变化。最近, 一项长达 18年的追踪研究发现 , GWAS-PS能够显著预测成人 (50岁以上 )的抑郁水平 , 累加遗传得分的解释率为 3%, 个体携带的风险基因越多(即 GWAS-PS越高), 其罹患高水平抑郁的风险越高(Levine et al., 2014)。
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同, Chang等人(2014)同样以来自 GAIN-MDD项目的探索性样本计算 GWAS- PS, 在 6989名女性被试中进行验证性分析 , 却没有发现 GWAS-PS与女性抑郁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 且这一结果不受抑郁测评方式 (二分法或连续记分法)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研究中验证性样本的性别比例不同。这一解释获得了有关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多基因研究的支持。Allison (2013)发现多巴胺候选基因 -PS能够显著预测全体被试 (51.6%女性)的 ADHD症状, 但是当分性别进行考察时 , 却发现候选基因-PS仅能预测男孩 ADHD症状, 而与女孩 ADHD症状的关联不显著。同时 , 研究结果的分歧表明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在遗传研究中 , 忽视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一致甚至出现不显著的结果 (Perry et al., 2013), 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多基因遗传得分与抑郁关联的性别差异问题。
此外, 对比两类多基因累加得分研究, 我们发现:与候选基因 -PS方法相比 , GWAS-PS方法并没有显著提高抑郁的遗传解释率。这可能源于 GWAS研究范式本身的一些限制。已有研究指出 , GWAS通常不能够验证已有候选基因位点 (Bosker et al., 2011; Hek et al., 2013; Wray et al., 2012), 甚至可能出现假阳性的结果 (Chang et al., 2014), 即包含一些与抑郁无关的干扰性基因位点。由此 , 如果 GWAS-PS中混杂了虚假的 SNP,其预测力可能被削弱 (Demirkan et al., 2011)。排除虚假候选基因干扰的最直接方法就是将具有真实效应的基因从假阳性结果中分离出来 , 而候选基因 -PS的方法考察的是科学研究证实的、具有真实效应的候选基因。足够大的样本量是 PS方法统计检验力的保证, 但是相比候选基因 -PS方法, GWAS-PS对样本量的要求更加严格 , 如 Dudbridge (2013)指出为保证 GWAS-PS的统计检验力 , 验证性样本的样本量要保证在 2000人以上 , 并且探索性和验证性样本需要具有相似的样本量。此外 , 探索性和验证性样本之间的被试异质性也是 GWAS-PS研究结果可靠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 , 研究发现 GWAS-PS对伴有攻击行为的 ADHD症状的预测力比对没有攻击行为的 ADHD症状的预测力高 (Hamshere et al., 2013)。此结果的可靠性依赖于探索性样本中不同亚类型的 ADHD患者的比例 , 但是通常情况下这一比例不可知 (Wray et al., 2014)。相比之下 , 候选基因-PS方法可以更加精确的定位某一精神障碍亚类型的候选基因。由此 , 有研究指出候选基因 -PS方法可以更有效的避免由样本量限制、被试异质性和人口结构等引起的误差 (Dudbridge, 2013)。这不仅解释了采用候选基因-PS方法获得的抑郁遗传解释率更高的原因 , 还提示与 GWAS-PS方法相比 , 候选基因 -PS的方法更具优势。
综上, 多基因交互研究与多基因遗传得分研究不仅为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而且发现多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模式具有多样性:既可能表现为非加性交互效应 , 也可能表现为累加效应。同时 , 上述研究提示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可能具有性别特异性。由此 , 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筛选真正与抑郁相关的候选基因 , 展开对多基因作用模式及其性别差异的考察。
2.2多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显示多基因与环境因素交互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 (Sullivan et al., 2013; Kaufman et al., 2006; Priess-Groben & Hyde, 2013)。采用基因 ×基因×环境(G×G×E)设计考察多基因对环境因素与抑郁关联的调节效应也成为了当前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
当前抑郁的多基因 ×环境交互研究涉及众多候选基因 , 其中 BDNF基因和 5-HTTLPR基因因为其在调节情绪障碍相关神经回路可塑性中的重要功能 (Martinowich & Lu, 2008)而备受关注 (见表
1)。Kaufman等人(2006)最早考察了 BDNF基因、 5-HTTLPR基因与环境对抑郁的交互效应。他们以 196名 5~15岁的儿童为被试 , 采用多主体报告的儿童期虐待史为环境指标 , 发现与其他基因型携带者相比, 同时携带 BDNF Met等位基因和 5-HTTLPR SS基因型的个体抑郁水平最高 , 但是这种多基因交互作用仅存在于遭受过虐待的儿童中。随后 , Kim等人(2007)对 732名韩国成人被试的研究重复验证了 Kaufman等人(2006)的结果。该研究显示在过去一年内经历较多的压力性事件后 , 同时携带 5-HTTLPR SS基因型和 BDNF Met/Met基因型的个体抑郁发病率最高 (约为 70%),而携带其他基因型的个体抑郁发病率小于 20%。然而 , 之后的验证性研究与早期研究结果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些研究并未发现显著的 BDNF×5-HTTLPR×环境三项交互效应 , 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导致抑郁的易感基因型与早期研究截然相反。如 Aguilera等(2009)和 Nederhof, Bouma, Oldehinkel和 Ormel (2010)的研究一致表明 5-HTTLPR基因、BDNF基因与童年期不利环境 (情绪虐待或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不能预测成人或的抑郁水平。Buchmann等(2013)对 259名成人初显期 (emerging adulthood)被试的研究显示, 相比其他基因型携带者 , 同时携带 BDNF Val/Val基因型和 5-HTTLPR LL基因型的个体在经历较多的早期心理社会压力后 (如单亲家庭、父母低教育水平 ), 其罹患抑郁的风险最高 , 而 BDNF Met等位基因和 5-HTTLPR S等位基因能够保护个体不受消极环境的影响。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 我们推测:环境测量与抑郁测量间的时间跨度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分歧的原因之一。著名心理学家 Monroe和 Reid (2008)指出, 与早期环境指标相比 , 近期环境对抑郁的预测力更强。最初 Kaufman等人(2006)测量了童年期虐待和儿童抑郁水平 , 环境测量和抑郁测量间的时间跨度小 , 由此童年期虐待是近期环境风险。后期的重复验证性研究虽然也选用了童年期虐待或者童年期压力性事件作为环境指标, 但考察的却是成人或青少年抑郁 , 环境测量和抑郁测量间的时间跨度大 , 由此可能表现为这些早期环境指标与 5-HTTLPR、BDNF间三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Aguilera et al., 2009; Nederhof et al., 2010)。值得指出的是 , 与多数研究不同 , Kim等人 (2007)采用近期环境指标(近一年的压力性事件)对成人抑郁的研究发现了与 Kaufman等(2006)一致的结果 , 支持了环境与抑郁测量间的时间跨度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其次 , 被试的年龄差异可能是造成研究结果分歧的另一原因。研究发现大脑皮层中的 BDNF含量具有发展动态性 , 与其他年龄阶段 (童年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晚期 )不同, 在成人初显期 , BDNF水平达到峰值 , 在这一特殊时期 BDNF含量的增加可能对这一时期心理障碍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Webster, Weickert, Herman, & Kleinman, 2002), 甚至可能影响 BDNF基因的功能, 使得在生命早期具有风险性的 BDNF基因型在特殊年龄阶段表现出保护性功能(Casey et al., 2009)。这可能解释了 Buchmann等人(2013)采用成人初显期被试发现截然相反风险基因型的结果。由此 , 我们推测 BDNF基因的功能可能存在发展动态性 , 未来研究需要采用纵向追踪研究进一步考察 BDNF基因、 5-HTTLPR基因与环境因素对抑郁的交互效应是否存在年龄差异。
表 1 BDNF基因、5-HTTLPR基因与环境对抑郁的三项交互作用研究概览表
| 研究 | 被试年龄 | 样本量 | 环境 | 早期/近期环 | 研究结果 |
| Kaufman et al. (2006) | 儿童(平均年龄 9.3岁) | 196 (51%女性) | 儿童期虐待 | 童年期(近期) | 携带 5-HTTLPR SS基因型与 BDNF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在经历儿童虐待后抑郁水平最高。 |
| Kim et al. (2007) | 成人 (65岁以上) | 732 | 压力性生活事件 | 过去一年内 (近期) | 携带 5-HTTLPR SS基因型与 BDNF Met/Met基因型的个体在经历压力性事件后抑郁风险最高。 |
| Wichers et al. (2008) | 成人(18~46岁) | 394 (100%女性) | 童年期经历 (包括虐待) | 童年期(早期) | 携带 5-HTTLPR SL基因型与 BDNF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在经历不良事件后抑郁水平最高。 |
| Aguilera et al. (2009) | 成人(平均年龄 22.9岁) | 534 (55%女性) | 童年期不利事件 (情绪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 | 童年期(早期) | 未发现 BDNF、5-HTTLPR和童年不利事件间的三者交互作用。 |
| Nederhof et al. (2010) | 青少年(平均年龄 13.6岁) | 1096 (53%女性) | 母亲孕期不利事件 (孕期吸烟和饮酒 )、童年期压力事件等 | 出生前和童年期(早期) | 未发现 BDNF、5-HTTLPR和孕期 /童年不利事件间的三者交互作用。 |
| Grabe et al. (2012) | 成人(平均年龄 55.6岁) | 2035 (52.5%女性) | 童年期虐待 (包括情绪虐待、身体虐待和性虐待) | 童年期(早期) | 女性:在携带 BDNF Val/Val基因型的个体中, 携带 5-HTTLPR SS基因型的个体在经历虐待后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 , 而在携带 BDNF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中, 5-HTTLPR SS基因型能够保护个体不受风险环境的消极影响。男性:未发现 BDNF、5-HTTLPR和虐待间的三者交互作用。 |
| Comasco, .slund, Oreland, & Nilsson (2013) | 青少年 (17~18岁) | 1393(49.5%女性) | 家庭和性虐待 | 童年期(早期) | 在携带 BDNF Val/Val基因型的个体中 , 携带 5-HTTLPR SS基因型的个体在风险环境(不利的家庭关系和性虐待)中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 , 而在携带 BDNF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中 , 5-HTTLPR SS基因型能够保护个体不受风险环境的消极影响。这一交互在女性中更显著。 |
Buchmann et al. (2013) | 成人初显期 (19岁) | 259 (54%女性) | 早期心理社会压力 (如单亲家庭、父母低教育水平) | 童年期(早期) | 携带 BDNF Val/Val基因型和 5-HTTLPR LL基因型的个体在经历了高水平的不利事件后抑郁水平较高。 |
值得指出的是, 多数早期研究并未考察多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模式的性别差异 (Kaufman et al., 2006; Kim et al., 2007), 或者仅采用了女性被试 (Wichers et al., 2008)。然而, 近期的研究发现 BDNF×5-HTTLPR×环境对抑郁的交互效应可能与女性抑郁的关联更加密切。 Grabe等(2012)以童年期虐待的严重性程度 (无虐待、轻微、中等程度和严重的虐待 )为环境指标, 考察了多种童年期虐待 (包括情绪虐待、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与 5-HTTLPR、 BDNF基因对成人抑郁水平的影响, 发现在虐待环境中 , 5-HTTLPR SS基因型对女性抑郁水平的影响表现出保护性还是风险性依赖于个体携带的 BDNF基因型。具体表现为经历了较严重的情绪性虐待后 , 在携带 BDNF Val/Val基因型的个体中 , 5-HTTLPR SS基因型对女性抑郁产生了更加消极的影响。相反 , 在携带 BDNF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中, 5-HTTLPR SS基因型是女性抑郁的保护性因素, 而该交互作用在男性中不存在。与此类似 , Comasco等(2013)对青少年被试的研究亦发现 , 同时携带 5-HTTLPR SS基因型和 BDNF Val/Val基因型的个体在风险环境 (不利的家庭关系和性虐待)中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 , 而在携带 BDNF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中 , 5-HTTLPR SS基因型能够保护个体不受风险环境的消极影响 , 并且这一交互作用对女性抑郁水平的预测作用更强。此外 , 单基因研究亦发现 BDNF基因 (参见元分析 Verhagen et al., 2010)和 5-HTTLPR基因(参见综述曹衍淼 , 王美萍, 曹丛, 陈光辉 , 张文新, 2013)的功能与女性或雌性动物的抑郁水平相关联的证据。如动物研究发现雄性 BDNF基因敲除鼠表现出较高的活动性 , 而雌性 BDNF敲除鼠表现出较多的抑郁行为 (Monteggia et al., 2007)。人类研究显示 5-HTTLPR基因与女性抑郁的关联更加密切 (Baune et al., 2008)。这提示性别可能是 BDNF× 5-HTTLPR×环境交互效应的重要调节因素 , 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多基因与环境交互效应的性别差异。
迄今为止, 仅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多基因遗传得分与环境因素对抑郁的交互效应。 Peyrot等人 (2014)以 GWAS-PS与童年创伤经历为预测变量 , 对 1645名成人被试进行研究 , 发现在经历较多童年创伤后 , 多基因遗传得分较高的个体更可能罹患抑郁。多基因遗传得分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其他行为表型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 (Beaver & Belsky, 2012; Belsky & Beaver, 2011)。如 Belsky和 Beaver (2011)的研究采用多种候选基因 (DAT1、DRD2、 DRD4、5-HTTLPR和 MAOA), 考察候选基因 -PS与父母教养质量对调节能力的预测作用 , 结果发现个体携带的易感等位基因越多 , 越容易受到支持性教养的影响表现出更高的自我调节能力, 而经历更多消极教养时则表现出更低的自我调节能力。与此同时 , Belsky和 Beaver (2011)指出所谓的“多基因遗传得分 ”可能是一种可塑性得分 , 可塑性高的个体对环境表现出更高的敏感性 , 即符合“可塑基因 ”或“不同易感性模型 ”假设。基于此 , 未来研究应该增加多种积极和消极环境指标 , 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下 (如不同易感性模型 )考察多基因得分与环境交互效应对抑郁的影响。
多基因对抑郁的作用机制虽然有丰富的研究证据支持抑郁具有多基因遗传基础 , 但是目前对多基因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单基因研究提示内表型 (endophenotypes, 如认知、人格、脑功能等 )可能在基因与抑郁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Drabant et al., 2012; Eisenberger,Way, Taylor, Welch, & Lieberman, 2007)。通过梳理多基因与抑郁内表型的关联研究为探索多基因的作用路径提供了以下启示:
首先, 多种基因可能共同参与负责抑郁情绪加工的认知过程 , 进而导致抑郁。据我们所知 , 目前仅有一项研究直接考察了 “多基因.认知.抑郁”这一中介路径。 Juhasz等(2011)采用正常群体样本 , 以反思 (rumination)为中介变量 , 考察了与压力适应相关的多种遗传基因和抑郁的关联 , 结果显示 BDNF基因与 CREB1基因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responsiv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1, 腺苷酸反应成分结合蛋白 1)在预测反思特质时表现为累加效应 , 并且以反思为中介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近期 , 有研究考察了多基因与抑郁相关脑功能的关联 , 通过脑功能与抑郁的关联推测多基因起作用的中介机制。如 Surguladze等人 (2012)的研究发现, 在恐惧实验条件下 , 同时携带 5-HTTLPR S等位基因和 COMT Met等位基因的个体, 其前额叶(双侧前额叶皮层中下区 ).边缘系统(右侧杏仁核)的功能连通性(connectivity)降低。正如前额叶晚熟理论指出前额叶与边缘系统之间联通能力的降低可能导致个体具有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 并且对压力更加敏感(Andersen & Teicher, 2008; Petersen et al., 2012), 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
其次, 多种基因共同影响压力反应相关的神经生物蛋白含量或荷尔蒙活性。 Buchmann及其同事(2013)考察了 BDNF基因、5-HTTLPR基因与心理社会压力对血浆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含量 (plasma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plasma BDNF)的影响, 结果发现携带 BDNF Val/Val基因型和 5-HTTLPR LL基因型的个体在经历了较多心理社会压力后会表现出血浆 BDNF含量的下降。有证据表明 BDNF在个体应对压力的适应性反应中具有重要功能 (Duman, 2002), 并且血浆 BDNF水平的降低会引发抑郁 (Bocchio-Chiavetto et al., 2010)。由此 , 我们推测多基因 ×环境交互效应也可能通过调节神经生物蛋白 (如 BDNF)的含量影响抑郁发展。此外 , 皮质醇是与抑郁密切相关的一种压力荷尔蒙 (stress hormone)。近期 , 一项学前儿童研究显示 , 在实验室压力情境下 , 多种压力系统候选基因 -PS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女孩的皮质醇水平 , 但对男孩皮质醇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agliaccio et al., 2014)。已有文献一致表明女性抑郁发病率高于男性 (Angst et al., 2002; Kuehner, 2003), 上述多基因对皮质醇水平影响的性别差异与抑郁发病率的性别差异相一致 , 提示我们多基因遗传风险可能通过影响抑郁内表型间接导致抑郁的性别差异。
此外, 多基因可能影响抑郁相关的人格特征。Middeldorp等人(2011)采用 GWAS方法探索与五大人格相关的 SNP,将达到显著性阈限的多个 SNP计算多基因遗传得分 , 随后采用该多基因得分预测个体罹患重性抑郁的风险 , 结果发现与神经质相关的多基因遗传得分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重性抑郁。这一结果表明神经质与重性抑郁具有相似的遗传基础。此外 , 一项元分析发现较高的神经质得分是重性抑郁的人格特征之一 (Kotov, Gamez, Schmidt, & Watson, 2010)。基于此 , 我们推测神经质可能是遗传因素影响抑郁的重要中介变量。
上述研究涉及了多种抑郁内表型 , 显示了多基因通过认知功能、荷尔蒙和人格特质等因素间接影响个体抑郁水平的作用路径。同时 , 这些内表型之间可能具有一定内部联系 , 而非简单的提供了多条影响抑郁的路径。如 Hyde, Mezulis和 Abramson (2008)的抑郁 ABC模型 (affective, biological, and cognitive model)指出遗传因素影响个体气质(情绪性因素 ), 而气质或人格特征又可以通过消极认知风格或反思 (认知因素 )间接影响抑郁。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开展关于“多基因.内表型.抑郁”的中介路径研究 , 并考虑多种内表型间的内在联系 , 以丰富抑郁的易感因素及其多基因作用机制的研究。
小结与展望
抑郁具有复杂的多基因遗传基础 , 来自多基因.抑郁的直接关联研究和多基因 ×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不仅为此提供了丰富的支持 , 还显示多基因遗传机制受到环境因素的调节并表现出性别差异。通过对 “多基因.内表型.抑郁”中介路径的分析, 本研究发现多基因遗传因素可能通过脑功能、人格特质和神经生物蛋白间接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和分析 , 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探索以下几方面问题:
(1)考察抑郁多基因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
多基因遗传得分和多基因 ×环境交互效应研究一致表明: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具有性别特异性。Priess-Grobe和 Hyde (2013)有关 5-HTTLPR× MAOA×性别×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研究证实了多基因 ×环境交互模式具有性别差异。该研究发现, 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 同时携带低活性 MAOA基因型与 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抑郁水平增高 , 而同时携带低活性 MAOA基因型与 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抑郁水平较高。该研究提示相同的基因对男女抑郁的作用模式存在差异。近期研究还表明男性和女性可能具有不同的抑郁易感基因。如前述研究显示 BDNF基因和 5-HTTLPR基因可能与女性抑郁关联密切(Comasco et al., 2013; Grabe et al., 2012), 而来自抑郁相关精神障碍 (如药物成瘾 )的多基因遗传研究显示多巴胺系统基因 (如 DRD2、DRD4和 COMT)可能是男性精神障碍的易感基因 (Conner, Hellemann, Ritchie, & Noble, 2010)。迄今为止 , 对抑郁多基因遗传机制性别差异的研究极少 , 而忽视性别特异性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一致 (Perry et al., 2013)。因此, 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考察性别在多基因遗传机制中的调节作用。
(2)考察抑郁的多基因.多环境相互作用机制。
由前可知, 多数研究采用多基因.单环境交互作用范式考察多种基因对环境和抑郁关联的调节效应。然而, 根据生态系统论(Bronfenbrenner, 1979)和发展情境论(Lerner, 2002/2011), 不同的发展背景之间相互作用影响个体的发展。著名心理学家 Moffitt, Caspi和 Rutter (2006)在其基因 ×环境交互研究的综述中指出远端环境 (历史、文化特征)可能通过近端环境 (社会和个人经历 )间接影响行为表型。近期 , 国内研究者也发现家庭环境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既可能表现出交互效应模式 (增强模式或补偿模式 ) (田录梅 , 陈光辉, 王姝琼 , 刘海娇 , 张文新, 2012), 也可能表现为间接效应模式 (父母支持通过友谊质量间接影响抑郁水平 ) (田录梅 , 张文新, 陈光辉 , 2014), 并且多种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模式会因为不同性别、情绪适应问题和年龄阶段而不同 (田录梅等 , 2012, 2014)。但是, 据我们所知, 目前仅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多种环境因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对多基因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 Kaufman等人(2006)检验了社会支持对 BDNF×5-HTTLPR×童年虐待的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社会支持能够缓冲携带风险基因的儿童在经历虐待后罹患抑郁的风险。基于此 , 未来研究应该采用多种基因指标、多种环境变量深入考察多基因和多种环境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抑郁的影响。
(3)增加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多基因遗传机制研究。
前述研究提示, 遗传基因与抑郁的关联可能表现为年龄阶段的函数。双生子和分子遗传学研究均证实了遗传因素对抑郁的影响存在发展动态性。早期 , Silberg等人(1999)对青少年双生子的研究显示 , 从童年期到抑郁的发展存在一种基因×年龄阶段×性别的交互效应 , 具体表现为抑郁的遗传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 , 并且这种遗传率的增加只出现在青春期的女孩身上。最近 , Zhang等人(2015)对 11~13岁青少年抑郁的追踪研究亦发现 , DRD2基因与母亲消极教养的交互效应能够显著预测 11、12岁青少年的抑郁水平 , 而在 13岁时基因 ×环境效应不显著。正如前述多基因×环境交互研究提示,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 抑郁相关等位基因可能表现出功能的反转。近期的单基因研究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 , Hilt, Sander, Nolen-Hoeksema和 Simen (2007)发现在青少年中 , 与 Val/Met基因型相比 , Val/Val基因型与较高的抑郁水平和较高的反思得分有关 , 然而, 在成年中, Val/Val基因型则具有保护性功能。目前 , 仅有一项横断研究考察了多基因对中年期和老年期个体抑郁的作用 , 并且没有发现基因解释率的年龄差异(Demirkan et al., 2011)。但是该研究只考察了成人样本 , 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年龄阶段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综上 , 采用追踪研究设计考察多基因遗传机制的动态变化对深入探索抑郁的多基因遗传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现有抑郁遗传机制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抑郁进行明确区分 , 尽管多数研究发现重性抑郁 (Fan et al., 2010)和抑郁情绪 (Priess-Groben & Hyde, 2013)具有同样的风险基因 , 但是目前多基因研究也显示遗传因素对抑郁的影响随着其严重程度而增大 (Chang et al., 2014)。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抑郁病人与正常群体中 “多基因.人格”研究显示出了不同的结果。如 Reuter, Schmitz, Corr和 Hennig (2007)对健康被试的研究发现 COMT基因与 DRD2基因能够交互预测个体抑郁相关人格特质 , 即风险规避和新异寻求 , 而 Light等人(2007)采用抑郁病人为样本的研究却发现 COMT与 DRD2的交互作用不能显著预测个体的新异寻求和风险规避得分。这说明尽管具有相同的风险基因 , 但是在重性抑郁和抑郁情绪中可能也存在着不同的中介机制 , 因而区分不同类型的抑郁可能丰富现有的多基因遗传机制研究。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