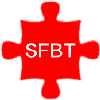女儿眼中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与葛雷果理·贝特生的奇妙组合
大多数人提到二十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时,大概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她出生于那个世纪初始的一九○一年,在二十八岁时即以《萨摩亚人的成年》(Growing Up in Samoa)一炮而红。此后将近半个世纪里,她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不仅左右了人类学的发展,也在其他相关学门,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精神医学,留下深刻的烙痕。透过经年累月的演讲、评论,及与种种媒体不倦的交流互动,她的想法也广泛地改变了近几十年来一般大众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历久不衰。
米德的魅力与原创力由何而来?在炫灿的外表下,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她的个人生活,尤其是感情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这些问题的答案,直到一九九四年她唯一的女儿玛丽.凯瑟琳.贝特生(MaryCatherine ;1939-,也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人类学家)出版了有关其父母亲的回忆录之后,才逐渐有一些轮廓。最近重阅此书,又读了米德晚年论及她自己前半生的自传,才对米德其人,以及与她齐名的第三任丈夫葛雷果理.贝特生(GregoryBateson;1904-1980)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有比较多的了解。
荳蔻年华在萨摩亚
米德双亲都来自新英格兰的书香世家。父亲是宾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母亲则「相夫教子」之外,还终生致力于女权及移民权益之推动。米德是五姊弟中的老大,从小灵巧精明又勇于任事,家中事务无分巨细,几乎无事不与,十岁出头就常女代母职,俨然如一家之主,尤其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精神抖擞,里里外外,打点一切。她也似乎从来就是个「守口如瓶」的人。高中的时候,她与其数学老师的弟弟路瑟.克瑞斯曼(LutherCressman;1897-1994;后亦成为知名考古学家)一见钟情,秘密订婚,此后数年,每日书信往返。但是直到她大学快毕业,两人就要结婚之前不久,居然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恋情。
也就在这大学的最后一年,因为学分的需要,米德选修当时还十分冷门的人类学,没想到居然发现这就正是她一直以来梦寐以求,足以「献身」的使命。此时文化人类学正面临转型,「文化演进论」渐为「文化相对论」所取代,研究方法也由前此从二手资料臆测、建构理论,转为以「身历其境」的细致观察为基础的「田野工作」,来描述、理解身处不同文化的人,其行为及思考方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化人类学家必须把自己一个人长期沉浸在当地的文化里,食衣住
行育乐,尽可能完全地「当地化」。研究者由此而有可能以「圈内人」的眼光来厘清许多由外人看来似乎「荒诞无理」的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
研究者以自身为工具,为了观察与记录,必须主动参与。参与和观察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参与会干扰观察的客观性,但是少了参与,就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多么具挑战性啊!而与此同时,学者忧虑许多「原始」文化因受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正在急速消失,使得这样的研究更具其急迫性。二十出头的米德,深切感受这使命的急切性与挑战性,她跃跃欲试。她不只是要去一个「原始」的部落,更是一个最遥远、最少为人知的「海角天涯」。那会是什么地方呢?她反复思量,决定那应该是南太平洋里最偏远的某一个小岛。主意既定,她就开始跟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时已德高望重,后被视为「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的法兰兹.鲍亚士(FranzBoas; 1858-1942)死赖活缠,将近两年。也就在这期间,她与鲍亚士的助教,后以《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Sword )等巨着享誉国际的茹丝.本笃(Ruth Benedict;1887-1948)结为终生的挚友。《菊与刀》一书之原始资料促成美军保留日本天皇颜面之决定,从而使日军得以循序投降。
一九二五年,一生严谨行事、待人不假颜色的鲍亚士,耐不住米德的坚持,居然同意让时年二十四岁,尚无田野经验的米德只身远行,在美属萨摩亚的一个离岛小村居住将近一年,亲身体验岛民生活的点点滴滴。鲍亚士交代给她的特殊任务是要去观察、记录萨摩亚及笄少女如何面对、如何成长。在近代欧美文化里,青春期是一个充满挣扎与痛苦的人生的阶段。鲍亚士希望借助文化间的比较来了解这个过程有多少取决于先天(也应该就有其普世性)的因素,又有多
少是后天(也就可能是源自文化教养)的影响。
从加州经夏威夷去到帕果帕果(Pago Pago,美属萨摩亚首府),在那里好不容易等到三星期才一班的补给船载她到目的地马努阿群岛(Manu'a)时,米德真正的旅程才终于开始。自此她日日夜夜穿草裙、打赤脚、编藤席、吃芋头、捕鱼、户外洗澡、观日落、夜夜歌舞、咿呀学语。她的起居工作室就在村里唯一的医疗站之旁。村民逐渐习惯顺道来访,这其中包括了一群青春期前后的少女。因为年纪相去不远,她们讲话的内容愈来愈无顾忌。米德惊奇地发现,她们对于男欢女爱的细节,一清二楚。她们虽尚未婚,却多已有相当丰富的性经验。米德如获至宝,逐字详录。她果然找到了她的恩师鲍亚士、她的挚友本笃,及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少年维特的烦恼」果然真的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米德文思泉涌,振笔疾书。她本来就有文学语言的天分,这下找到了着力点,尽情发挥,翌年返美,书已成稿。《萨摩亚人的成年》于一九二八年初版,轰动一时。此后经常再版,并译成多国文字,畅销迄今。这本书之所以广受注目,历久不衰,固然一部分源于其研究的细致及作者写作的才华,但更重要的应该是此书为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对人性的乐观精神及个人主义提供了具体的左证。它试图说服世人,我们的行为及对生命历程的反应,不是先天注定的,不是一成不变、无可动摇的。既然我们现在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所以会经历那么多挣扎、那么多风暴,是因为我们的「礼教」强加在他们身上,千钧万鼎,喘息不得,那么我们不就应该考虑如何改造社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比较不受拘束,比较有选择,比较不需要耗费如此多的精力去做无谓的挣扎吗?米德由跨文化的角度来反思、批判当年美国社会文化,变成了西方新一代求变求新的代言人。她也以社会改造的推手自任,经常为报章杂志撰文、接受访问、公开为大众演讲,很快就成为时代的宠儿,带动时尚风潮,同时也使文化人类学从幽暗的学术角落走向大众,渐成显学。
在人头猎人的环伺下跃入爱河
米德由「有如天堂」的南太平洋小岛返回「文明世界」的路程崎岖漫长。从萨摩亚经澳洲横跨几个大洋,再经欧返美,船期一延再延,路线不断更改,沿途风暴不息,时有灭顶之虞。离开「异域」,她却开始染上了「乡愁」。她空有满肚子的奇闻异谈,无由与整船的「凡夫俗子」分享。这个缺憾,直至在雪梨遇到了来自纽西兰,同样满怀热忱的年轻心理学家里欧.福群(ReoFortune;1903-1979)时,才顿时改观。福群的学术兴趣,其时也正由心理学逐渐转向人类学,两人一见投缘,一路上有讲不完的话题。他们就这样绕过几乎整个澳洲,途经锡兰、也门、
西西里,终于抵达马赛,才怅然分手,各奔前程。米德的丈夫特意到马赛码头来接她。他们依原订的计划畅游巴黎之后,回美重拾旧梦。然而他们之间,已经隔着不知多少个大洋。他已不再是她的学生情人,夫妇之情已如东流江水,无可挽回。分手之后,米德旋即回到福群身旁。
萨摩亚之后,还会有什么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呢?米德与福群再婚后,两人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放到新几内亚。虽然知名的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兰尼斯洛.马林诺斯基(BranislawMalinosky; 1884-1942)前此不久才以他在新几内亚离岛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Islands)长住数年的素材写成他的成名大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新几内亚本岛的内陆则尚鲜为人知。此岛高山绵延,纵谷密布,人民散居各处,语言习俗天差地别,好猎人头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一九五一年米德与福群二度前往新几内亚,目标直指那最鲜为人知的深山丛林。他们全副装备,外加六个月的粮食补给,一路蜿蜒艰难上行,到了高山顶端,雇来的土著运夫一夜星散,夫妇俩进退失据,只得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落脚。他们俩原本就个性不合,经常磨擦(米德在她的回忆录里不断地描述福群的霸道自私),自此冲突全面爆发。翌年他们脱困下山,经过一番的整顿、装备,重新出发,随即撞上了葛雷果里.贝特生。贝特生是鼎鼎有名的英国遗传学家威廉.贝特生(WilliamBateson; 1861-1926)的三子,父母双方皆来自家学相传、人才辈出的名门。老贝特生正是那位以重新发现门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定律并将之发扬光大而享誉国际的科学家,也是首倡使用「遗传学」这个名词的人。他对三个儿子冀望甚深,然而葛雷果里的大哥不幸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几近结束时阵亡。两年后他的二哥又因志在诗文,不愿继承其父之衣钵,特意选在大哥生日那一天,在伦敦最热闹的巿中心饮弹自尽。此后葛雷果里成为父母亲唯一的冀望。虽然他与二哥类似,也喜好文学,却不得不屈从于父母,成为一个稍有所成的生物学家。当他在科学与文艺的夹缝中发现人类学时,欣喜莫名。以此为由,他也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漂流到天之涯、海之角。
温和、散漫的贝特生,居然能够在好战的人头猎人中生存,或许已经是个奇迹了吧(当然,他那近两百公分的块头,或许会有点帮助)。他的确保住了他的人头,也捱得过疟疾、赤痢等等热带疾病的折磨。但是如果米德与福群没有适时出现,他是否能捱得过寂寞,也许会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他对米德体贴入微,也与福群无话不谈,没日没夜。他本来对自己毫无信心,觉得他在新几内亚虽然已经好几年,却仍摸不清自己所为何事,方向何在。米德美国式的乐观进取感染了他,让他重拾往昔的信心、热情。三个人来自天南地北,气质禀性天差地别,互相吸引、互相学习、互相激励。欢乐中夹杂着嫉妒与竞争,孕育出奇思异想,也照明了他们各自的方向。而在这个过程中,米德与贝特生愈走愈近,终于就把福群排除掉了。
因为米德的支撑、鼓励,贝特生终于能将他多年在新几内亚收集的资料与经验理出头绪,完成他的处女作《那温》(Naven),作为他送给米德的结婚礼物。这本长达三百七十五页的书,详实描述雅特穆尔族(Iatmul,一个直至二十世纪初仍盛行猎人头、食人肉的部族)的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婚丧节庆、音乐艺术(他们的雕刻可是鼎鼎有名的)。但是这本书最让人惊异的是,在这好勇斗狠,似乎父权至上的社会里,「那温」这种最重要的节庆仪式,却是以男女角色的互换为主轴。大至获得一个新的首级,小到渔猎或西米(sago)丰收,全村都可以「那温」一番。此时「英雄」的舅舅们争先恐后地穿上妇人的草裙,竞相表现他们的妩媚,而他的姑姑们则穿戴勇士的服饰,挥舞着长辈的令牌。这样的习俗,到底有什么意涵?村民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无从解释,也不必解释。贝特生的书引经据典,天文地理,洋洋洒洒,给读者的是一头雾水。米德的臆测简单明了:正是这出乎常情的角色互换,让身处其中的族人更能体会性别的差异及其重要性。
米德也没有闲着,那几年里她文思泉涌,又出版了好多本书,其中尤以《性别与气质》(Sex andTemperament)一书最负盛名。此书详述在三个不同的新几内亚文化里的男女角色、及分工。第一个如大多数社会,「男尊女卑」。第二个则是男女平权,事无巨细,无不分工。然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她也发现了一个部落,其性别角色「男卑女尊」,大异于一般习见的传统。
此书一出,女权主义者振奋莫名(她们振振有辞地说,米德的数据证明所谓「母性之爱」,只是社会加在女人身上的链锁),「卫道之士」对米德就更憎恨有加了。但是不论如何解读,相对于十九世纪末开始盛行的「先天」(大体指遗传)决定论(佛洛伊德甚至说anatomyisdestiny,「解剖学」决定命运」),揭示了「环境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时代的来临。这个新的思潮,推到了极端,视初生儿为一张白纸,社会、文化透过父母、亲友、学校,不但决定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也形塑他们的性格、气质。而婴幼期自然就是这「社会化」过程里最重要的阶段。如此说来,现代人所面对的种种心理、行为问题,就都可溯源自婴幼期的亲子关系。为预防精神疾病、增进心理健康,我们就应该努力研究在现代社会里如何成长,提倡有利于健全发展的亲子互动方式(当然,在当时的「文明」世界里,其实就是意指母子关系)。由是,米德理所当然地相信,文化人类学可以透过改变人们的育婴方法来造福世界。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