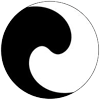:整体情境
Transference: The Total Situation 移情:整体情境
文章来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66:447-454(1985)
作者:BettyJoseph
译者:何巧丽
历史:起初Freud把移情作为阻抗,而后视作必须的分析工具, 观察病人与原始客体的如何丰满的呈现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Klein认为通过投射和内射,每个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内部客体,Strachey引用了了这一观点,认为被“转移”的并非主要是过往的外部客体,而是内部客体;而内部客体被建构的方式有助于理解分析如何促发转变。
Klein对早期和早期心理机制的研究,主要是,她的研究扩展了我们对移情的本质和过程的理解;Klein在“移情的起源”一文中说道:“我的经验是,在阐述移情的细节时,一定要从‘整体情境’的角度来考虑,是过去的经历带着防御和客体关系的印记以整体情境的方式转移到当下”,作者希望进一步阐述;“整体情境”大意指病人带入治疗关系的所有东西;若要理解移情,就要理解病人如何把我们拉进他们的防御系统、如何的在移情中对我们见诸行动、试图让我们也对他们见诸行动;如何传达他们内部世界的方方面面,这一内部世界从时候就开始建立,又经过童年期及成年期的不断修整,而这些体验往往是难以言表的,只能通过包围着我们的感觉,通过我们的捕捉到,通过言外之意交流。
反移情一开始也被视为阻抗,现在则被认为是分析所必须的工具。更进一步说,觉察“我们自己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治疗室中发生了什么”,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发现移情的方方面面;因为变动是移情关系的重要特征,所以所有的解释都不可能只是单纯的解释和说明,而必须是根据病人情况特别设计的,能和病人的方式产生共鸣的;治疗师可以试着觉察病人如何使用移情,判断病人的功能水平及其特质;明显的移情的变化是引发真实心理变化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从整体情境的角度来考虑移情,上述问题就会更清晰。
我用一个简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现存的焦虑和内部客体关系的整体特质是如何活现于移情中,尽管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的联想及相关人物似乎也需要解释。这个案子是研究生研讨会上一个同学提供的,其中对于该个案治疗似乎很难充分地帮助到这位病人:分裂、愤怒、童年期父母在情感方面的缺失。分析师对自己的一次访谈的过程和结果不太满意,把它拿来讨论,病人的个人情况很详尽。
研讨会上,大家感觉对于个案的解释是相当好的,敏锐而丰富;于是大家试图进一步去理解,提出各种观点,但是所有想法都让人感觉不那么尽如人意;渐渐的,大家意识到,这些现象或许是一个线索:——研讨会的困境反映的是移情关系中的分析困境——而这可能又是病人内心世界的投射,即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无法赋意——即在展现母亲难以,无法理解,但是却装作是理解的,就像研讨会上发生的事情;病人发展出防御:讲述一些看似有逻辑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但是讲述的过程防御了那种不被理解的感受,让病人可以抓一个东西在手里);若分析师竭力为病人的联想给出详尽的解释,那么她就活现于病人的防御体系,为这些不可理解的感受制造出一些虚假的理解,而不去碰触病人那种生活在无法理解的世界之中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让治疗师感觉不舒服,相信自己理解了病人提供的素材要比成为不能理解小孩的妈妈要舒服的多。
反移情:理解移情的线索在于关注研讨会上明显的现象,即感受到迫切地要去猜测、挣扎着去理解而没有贴近病人的联想,而联想有可能会带来感受。我们想要猜测的愿望,迫切的想要理解病人,这些反移情让我们感觉到,这是对于病人内心世界和痛苦部分的投射性认同。
我假定此类的投射性认同是的,无法言说的。若只与病人可言表化的这部分工作,就无法考虑到移情关系中行动话的客体关系,在这个例子中即没有理解能力的母亲和感觉无法被理解的婴儿,这是病人的根基;若未触及这些部分,治疗可能会产生表面的变化,但是不会出现真正的心理改变;病人早期关系存在严重的问题,而后在其上建立了表面正常但虚假的人格结构,由此病人不至于崩溃,能够在生活中许多方面或多或少正常发挥功能;解释若只处理个人联想,那么只会触及病人成人的人格部分,真正需要被理解的部分则是通过给分析师施加压力来表达的;在此可以看到,病人早期客体关系的性质、防御组织、表达整个冲突的方法,这些活现在移情中。
再举另一个病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一开始,通过病人所建立的与过去相关的氛围,移情以一种特殊的理想化的方式被体验到,而当这种移情崩溃后,病人的防御和早期客体关系中原始的部分怎样浮现出来,活现于移情中,并且试图拉着分析师一起去见诸行动,而后针对这一点做工作,带来更多的动力,病人的内部客体也发生了暂时性的变化。
这个病人我把他称为N,进行了多年的分析,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但是总不稳固,没有那个问题被彻底修通了,结束也遥遥无期;我注意到自己有一种模糊的舒服感,好像我很喜欢与这个病人的访谈,对访谈满意,虽然我需要吃力地和他工作;当我反思我的反移情时,我觉察此满意感必定呼应了病人内心的某种信念,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是满意的;他有特别的地方,对此我的解释仅仅是解释;他这个地方是确定的、无需改变的。(若深处潜意识的信念不被考察,治疗不会成功,而只有貌似正确的解释而已)这些信念也使他认为,我对他有特别的和喜爱,我不希望他离开;这是分析师舒服的反移情的根基。
关于解释:移情和解释是生动的、体验式的,不断变动的,因此解释必须传达出这些特质;患者洞察到自己潜意识的信念:自己有特别的地方,治疗有一种模糊的不真实性、我对他有一种依恋,都一一痛苦地浮现出来;若把这些和他的过往史迅速连接起来,应当是蛮舒服的,小小孩,对妈妈的喜爱,妈妈和爸爸关系恶劣,爸爸非常严厉;但若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就再一次正中N的下怀,从而解释不过是解释而已;重要的是,首先把潜在的信念暴露出来,不管多么痛苦,由此病人可以在移情中真切地体验到,之后慢慢地再与其历史相连。
洞察之后:下面我将呈现N之后的一个治疗片段,来说明当全能的、关于自己特别之处的幻想从移情中退却之后,早期的焦虑、进一步的心理冲突如何进入到移情中,出现在梦中,以及梦的内容如何活现在移情之中;此时,尽管有上述洞察,N仍然陷入一种被动的、绝望的受虐当中;某一次的治疗中病人带来一个梦。
梦:好像发生了战争,病人正在海边的一所房子里参加会议,所有人都围桌而坐,听到屋外直升机的轰鸣声,通过声音判断,直升机出了故障,病人和一位长官离开会议桌向窗外看去,会议还在继续。直升机遇到了麻烦,飞行员跳伞,更高处有两架飞机,俯瞰着直升机,但他们太高了,看起来很小,无法提供任何帮助,飞行员掉入水中,N纠结于飞行员是否打开了气囊,或者已经死了等等。
我就不提供我的解释所依据的素材了,大致上,我让N看到:梦中的战争隐喻我和他之间的战争;N倾向于背对会议,即背对治疗;病人向外看,看到出了问题(直升机),看到分析师(两架飞机),两个飞机即两个胳膊和乳房,俯瞰着他,试图去帮助他,但他沉浸在自身的某一方面,那个飞行员,遇到麻烦、正在坠落的、死去,这是他受虐愿望的幻想世界;病人的梦显示病人选择沉浸在痛苦的崩溃,而不是享受帮助和进步。
解释之后N的后续反应:似乎渐渐被这些解释所触动,感受到这些受虐幻想对自己的重要性;接着,第二天他讲到这次分析及对梦工作后他感到很不平静,他从各个角度谈到这次治疗以及他对和咨询师之间的战争的关注,他感觉非常糟糕、不管分析中发生了什么,他总是陷入拒绝和冲突中,进一步还谈到了自己在觉察到在卷入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种兴奋感;这似乎是一些洞察,在某方面是的,但从他平淡,甚至无聊的语调中,我感觉到他说的都是重复我以前说过的话,实际上这些表面上的洞察被用来抵制治疗的进展,像是与我的一场无声的战争;我把这些呈现给病人看,病人声音忧郁的回应:看起来我不想继续,不想合作……等等。我听到我自己开始向病人呈现:并非如此,因为他毕竟来参加分析;后来,渐渐意识到我扮演了他的积极部分,这一有能力去、去工作的部分被投射在我的身上,由此他无须再为此负责,亦无须承认;或者我就得认可他确实不想合作,无论怎样都不是出路。
病人看到这些之后,说他无能为力,他很明白,但他感到,他明白我的意思……治疗陷入僵局,理解但无能为力。此情此景类同于前面的梦,沉迷于关注即将溺亡的飞行员,我高高在上,无能为力,现在N则沉迷于他自己的话语“我明白,但是我无能为力”;梦正在移情中活现。
我让病人看到:通过这些言语,他正积极地为我设套,而这恰恰证明了我们之间的战争;来来回回之后,N按他自己说是“无明显原因”的,想起一段经历,是关于一只烟盒;当时他正在寄宿学校,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会拿一个锡制的罐子或硬纸盒,用帆布仔细的包裹起来,然后他会在书中挖一个洞,把他的烟盒藏在里面,他会一个人到郊外去,坐一会儿,有时会躲在老灌木丛后抽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抽烟。他感到孤独,这种感觉犹新,他接着补充道:吸烟似乎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
我让N看到,当我让他明白他在给我设套时,我认为他对此的反应有困难,等等。他终于认识到,争斗和设套似乎有某种兴奋,但重要的是这种兴奋在治疗过程中减少了,对其上瘾降低了,但无法放弃,若放弃就意味着屈服于老人(即治疗师),正如他从吸烟中没有什么真正的快乐,但总是偷偷地去做;移情中的问题在于如果认可并承认其治疗进展,就意味着他要放弃挫败我的快乐;正如本次治疗起初,他更愿意去讲糟糕的地方、虐待和兴奋而不愿意叹气他的进步;他仍不愿意放弃这些,不愿去享受好起来的感觉帮助,就像梦中的飞机。
N倾向于同意这一点,说这次治疗快结束时,有些东西改变了,他发现他的发生了变化,阻滞感消失了,但是又感到悲伤、愤怒,抱怨我对烟盒这段记忆关注不够,这段记忆对他来说鲜明生动,也很重要,而我却一带而过。我又回到这段记忆,去了解他的感受,查看我是否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也提醒他,他压抑了他的兴奋,而我听他讲述这段毫无乐趣的吸烟的历史的时候感到很多的快乐。我也让他看到他不愿承认自己感觉已经发生改变,他已经没有那种不舒服的阻滞感了。
N同意,但他说:“我还是觉得你太快了”。N承认愤怒可能和治疗带给他的改变有关——疏通了阻滞的感觉——但“太快了”,他解释说:治疗师就像花衣魔笛手,N则任由治疗师拖着走。
引诱:我指出:听起来似乎他感觉我并没有真正分析他的阻滞问题,而是把他从他的位置拉走了、引诱走了;正如他感觉儿时被母亲引诱,正如他相信我和母亲对他都有特别的感受;N提到当时的又一种恐惧,即恐惧陷入一种兴奋的温暖感觉,一种他曾过去经称之为“小狗狗”的感觉。
我让他看到有两大焦虑,把他从先前心态引诱走及自己积极的、兴奋的、幼稚的、像“小狗狗”似的感受;这些感受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关注,都是以前就有的重要感受,但是我认为他现在提出来,是为了把这些感受被投射到我身上,由此他无须再去承受、体验和表达那种在本次治疗后半段开始出现的真实的好的感受,特别是那种温暖和感激;再后来他觉察到飞机是可以提供帮助的;治疗接近末尾,N同意,深受触动,离开。
运用移情带来的好处:首先,在这个案例中,梦的内容活现于治疗,按照移情的方式,相当简洁的显示了它的隐意,即病人愿意沉溺于悲惨和问题,而不愿接触可提供帮助的、真实的客体;那些飞机,很小,无法提供帮助。分析,解释,当病人觉的他们像乳房一样提供营养和帮助时,他们却转身离开了。发觉到治疗师正在提供帮助之后,旧的问题如兴奋、悲伤、不合作便被鼓动起来对抗之;发现了人格好的方面,但是温暖地靠近客体的能力被歪曲、投射到我身上,变成是我拉拽、引诱他;但是真实的情况被巧妙的藏起来了,就像香烟盒被藏在了书本里(或许书本上古老的解释,现在已不在有意义了)。但是他很明白,这样做他并不快乐。这里我们找到了这些象征的隐意,我们也能够在移情中找到他们。我相信,病人获得了一定的洞察力,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选择,一靠近帮助性客体,二沉溺于绝望;但此时防御自动启动,病人选择后者,把分析师推向指责、批评的立场,拉进他受虐式防御之中;从后续的工作可以看出,直到其接受帮助和温暖,这些防御才减少;也就是说,在承认了帮助性客体之后,就能与其连接并内化,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
移情充满意义和过往的经历:是一个关于病人是如何离开、回避好的养育客体的故事,我怀疑事情总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有一点线索,那就是,通过把爱投射给妈妈并扭曲它,从而妈妈作为一个引诱者的形象得到巩固,也保留了对于的焦虑;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她对于她的儿子就是充当了诱惑性客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病人是怎么使用这一切的。什么时候,是否要多这些做出解释,是一个技术问题,我只能在这里探讨。我至始至终都在强调,移情是一种关系,其中有什么东西一直存在,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基于病人的过往及其与内部客体的关系或者是病人对这些的信念及想象。
我认为,我们需要帮我们的病人通过移情把自己和过去联系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连续感和独立感,以获得一部分独立,这样才能帮他们从以前对过去的混乱无序的感觉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困难要克服,包括技术上的和理论上的。例如:一个病人如果在婴儿时期没有好客体的体验,他是否有能力在移情中体验到好客体?对此我也心存疑虑。我的假设是:如果一个病人在婴儿时期没有遇到一个客体能够让他投射哪怕一点点的爱与挫折,那么,他不会来找我们接受分析。他会独自去寻找一种式的方法。但分析师能够做的是:跟随移情中的运动和冲突,让曾经被防御的感受或者转瞬即逝的感受再度复活,使这些感受在移情中扎根更深;我认为分析师不是全新的客体,只是被强化后的客体,因为更强烈的、深刻的情感在移情中被修通了。至于N,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温暖的感觉和价值感逐渐复活,而原来这些感受很微弱,且被防御在外。现在,我确信,这些情感得以解放并被加强,客体表征也相应发生了转变。
与历史相连:何时以及如何在解释中把当下的关系和过往的经历相连呢?若连接会打断治疗的流动过程,有可能沦为解释性的讨论或练习,就不要去连接;直到感受不再那么激烈,病人能充分地接触自己和当前的情况,并且想去理解、愿意和分析师一起努力做出连接,此时方可连接;即便如此,这仍有可能作为防御;这并非此文主旨。
这里我想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一个主题:当时我说通过移情我们既可以看到防御的本质同时又可以了解病人的心理运作机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另一个病人c的例子:在移情中,可以看到防御的性质、心理组织活动的水平;C有些强迫型人格的表现,他给自己的生活设定了很多限制,直到开始接受治疗,他才看到这种限制到了什么程度。不过我渐渐有一种印象,在强迫之下,有更加深层的恐惧。
案例C:c要求周五早上提前一刻钟开始治疗,他是周五早上的第一个治疗,为了赶上去曼彻斯特工作的列车;大量讲述有关赶火车、交通拥挤的焦虑,以及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的强迫性细节;担心失去会员资格,朋友变得不那么友好;分析师对于被排斥感、不想分离而想待在原处并且封闭内心的大量解释似乎无甚效果;当试图让他看到他希望待在内心,这样他更安全的时候,C开始流畅地讲述这个问题同样出现在他换工作、换职位、换衣服、换汽车等过程中,他总是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改变。
案例C解释:治疗呈现出有意思的场面,虽然C说得内容似乎准确而重要,但是想法不再被认真思考,它们变成了词汇、具体的可供分析的物体,C可以沉溺其中,就像躯体的心理伴随物,C可以退缩其中;分离的问题,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都被规避了,因为我们两个的想法被体验为完全协调的,并且他沉迷于这种协调之中。我向C解释了这些,很震惊,说:“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曼彻斯特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身体”;我认为这把尖刀不只是我把现实世界推回到他的脑海中,这也是插入我和他之间的尖刀,将我们分开,让其感到分离,这引起了即刻的焦虑。
强迫性的控制、使自己和分析师感到安心、回避分离和新事物、需要待在里边,对于这些的解释,C没有体验为帮助性的解释,而是把这些内容当做具体的物体、当做我的部分,C可以防御性地沉溺其中,从而抵御和分离有关的、更加具有广场恐怖症色彩的精神病性焦虑;可以看到两个水平的操作,即对于恐惧的强迫性防御活现于移情;当触及到更深的层次,当我指出其流畅地、防御性地使用我的话语,我的解释就像一把尖刀,焦虑出现于移情;若解释停留在个人联想的层面,没有考虑totalsituations以及分析师的话语被使用的方式,我们就会沉浸于虚假的成熟或者更加性的组织,从而忽视更具精神病性的焦虑和防御。
病人如何听解释:在本文中,我重点阐述移情中都发生了什么,在刚才的例子里,我想说明,直到病人接近抑郁位态,解释才会被听成单纯的解释。解释和移情本身变得更加现实而较少承载幻想性的内容;惯用原始防御(分裂、投射性认同)的病人常以不同的方式“听”或者“使用”这些解释,如果我们要搞清楚移情的状况及病人的状态及病人的认知是否正确,那么他们怎么“听”和“使用”,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必须清楚。病人有时以更偏执的方式来听这些解释,例如C,听懂了我关于曼彻斯特的解释,会当作批评和攻击;病人虽然被解释扰动,但是实际上听到了、有时候是正确地理解了,不过仍然在潜意识的层面活跃地使用它,将分析师也卷入其中。
我相信,N并没有把我关于直升机的梦的解释听成是残酷的,难以忍受的,但潜意识里,N利用这些解释去受虐一般地责备、打击和折磨自己,在幻想中将我“使用为”施虐者;C听到了部分的解释,但是并没有去思考这些话语,而是潜意识地使用这话语去行动化,并且试图把我引入这样的行为,旋转、把玩这些话语,但是没有真正的沟通;这些行为不仅渲染并且构成了移情情景,对于治疗技术也有重要意义。
SUMMARY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移情这一概念,在本文中,我想讨论我于的一些想法。我强调,移情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鲜活的关系,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病人的心理结构是基于他早年的经历及心理机制运作习惯,基于他的幻想,冲动,防御和冲突,我阐明了其中所有重要的内容是怎样在移情中以某种方式活现的。另外,对分析师是什么,分析师说了什么的回应,很有可能是按照病人自己的心理结构,而非按照分析师的意图或者分析师给出的解释的含义。因此,我也试图讨论我们的病人与我们交流问题的方式是如何常常超越了病人的个人联想,病难于言表,但是可以根据反移情来衡量。我认为,这几点是在移情的整体情境这个大标题下我们应该思考的。
Betty Joseph, bornMarch 7 1917, died April 4 2013.
家,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前主席。 她主要研究“病人如何发展出防御以抵制改变”,因为病人害怕随之而来的焦虑。
病人的投射会强烈的影响分析师,分析师可能发现自己正在逃避自己的困难,或者是一些吓人的想法和感受,而不能完全意识到治疗中发生了什么。BettyJoseph在抓住病人的投射方面非常有技巧。她认为探索并解释这一过程是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带来持久的心理改变。在病人和分析师互动的时候,采取这样细致的工作方式,需要分析师相当大的勇气,并要求分析师能够承受焦虑,怀疑及不确定性。
她认为只有非常严密的注意病人在治疗中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同时注意分析师自己的反移情,这样,心理现实才会显现。这个工作非常困难,因为病人的心理结构和防御会把分析师拉回到病人更能够忍受的部分,而心理改变和领悟总是引起混乱,并引发一种强烈的想要回到旧有的平衡状态的趋势。
要训练成熟的技术,需要治疗师完全的诚实,不仅因为分析师倾向于相信自己做的不错并试着接受病人为了让分析师安心而对解释的认可;还因为分析师部分被潜意识的压力影响,被病人想要保持现状而和分析师保持一致的愿望。这些反移情需要被严格的审查,当然这样做可能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