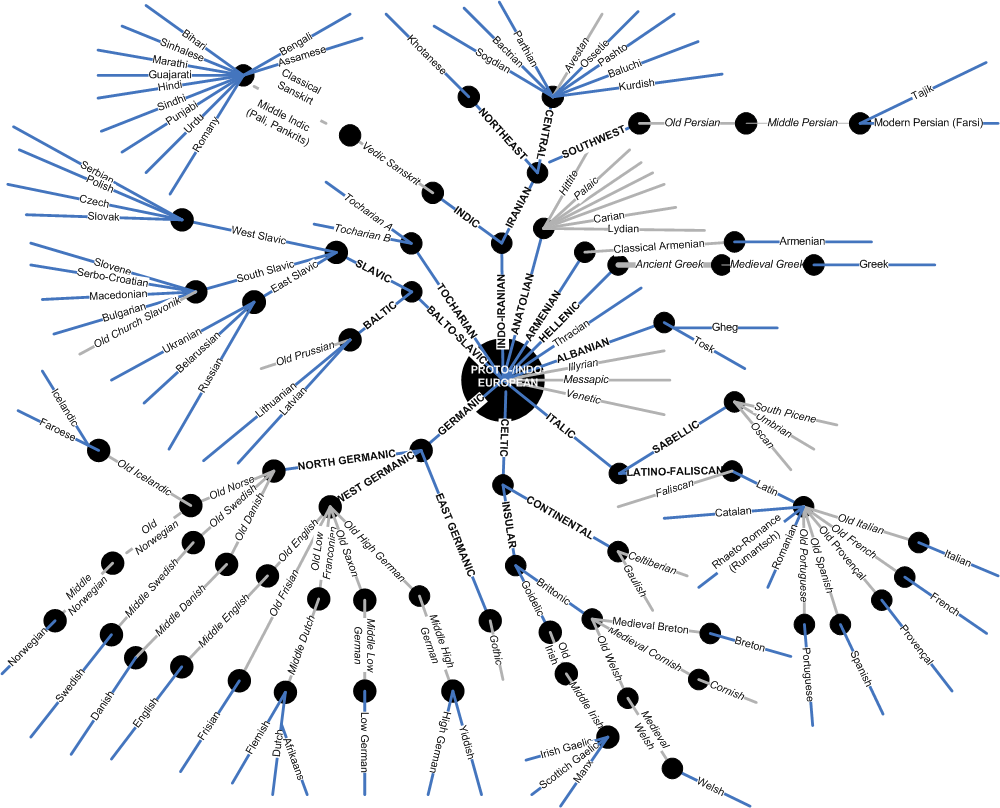认知语言学中值得思考的八个问题
四川外语学院 王 寅
(原载《外语研究》2005年4期)
摘 要:主要基于体验之上建立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已成主流学派,对语言作出了重大发展,但笔者也发现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本文将其归纳成八点,期望大家能解决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断完善认知语言学,或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做到有所发展。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 体验哲学 问题
主要基于体验哲学之上形成的认知语言学,对传统语言学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提出了很多解释语言的新思路,令人深受启发,对语言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期望它能解决全部问题,像所有的语言理论,认知语言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
1.认知的性问题
他们把“认知”的范围定得十分宽,并认为无意识性认知至少占95%,这与传统分析哲学中观点不同。问题是他们没有详细论述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剩下的那个不足5%又是什么样的认知,具有什么性质。这个95% 比例是否会因人而异,随情形有变化?如与成人是否会一样?普通人与哲学家、科学家是否不同?对不同事体(如日常简单事与理论研究)的认知和推理在有无意识性程度上是否有差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有较大程度的无意识性,但将其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在演说和报告时,在学习外语的初始阶段,似乎有较大程度的有意识性。
2.基于原型成员的延伸问题
依据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其中有一个中心成员,其它非中心成员则是依据这一中心成员向外延伸而形成的,我们当然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例略。但在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中人们往往很难确认中心成员,如“over”,很难说哪一个义项是中心成员,Brugman 是以“The plane flew over the city.”(over具有动态含义)开始论述的;Taylor则是以“The lamp hangs over the table.”(over具有静态含义)开始的,而且这一义项在很多词典中也常常被列在开头。抽象概念的原型该是什么样呢?原型范畴理论对“范畴内成员是基于共享特征”的批判基本是正确的,但有学者认为范畴中的所有成员都是以原型成员为中心向外延伸的,这一说法却值得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在一个多义范畴之中。上述的over就是其中的一例,我们不能确定一个中心成员(中心意义、基本意义、原始意义),因此也就说不上其它成员都是以一个原型成员为中心向外延伸而成的。
3.语义链问题
Taylor(1989:108)曾用“语义链”理论来解释多义范畴问题,他认为多义词 中的不同意义往往是通过“语义链”而形成的:意义A与意义B基于某一或某些共享属性,像链条一样关联;下去 :A B C D …… 。但语义链忽视了中间的过度过程,因为意义在引申过程中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从A变成了B,中间很可能会存在一个两者共存的阶段,即:A AB B,这一解释似乎更为合理。Langacker(1990:266-272)更为详细地描绘了语义网络的发展情况,这似乎比Taylor的语义链更为详细,更有解释力(C表示A、B两义项的某种范畴化关系,同样,L表示义项K和A之间的范畴化关系,参见Rice,1996:141):
Putz & Dirven 1996:141 下图
人类的思维可谓千变万化,语义延伸的情况错综复杂,同时各语言的语义网络延伸也会有很大差异,这种模式化的总结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描写,可能具有一般性规律,但还需要大量的语言实例来加以验证。另外,语义链,或语义网络模型,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1)Taylor的“语义链”也没能很好地解决所有词项范畴中“哪个意义为中心”的问题;同时他的表达式往往会给人一种互相替代的感觉。(2)如何确定语义延伸的界限?语义延伸到什么地方就不再属于同一个范畴了?或者说,一个范畴能容忍成员的变化度有多大?人们每次运用一个范畴时都要重新确定其变化度吗?(3) 究竟是什么机制可以决定一个范畴的范围?为什么有的词汇范畴大,有的词汇范畴小,该如何描写范畴成员密度问题?(4) 一个范畴中的成员是如何排列的?一个范畴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原型),还是可有多个中心,还是可有一个中心群(多个原型)?(5) 如何确定一个范畴中多成分间的概念距离?它们离中心的位置可以改变吗?如何改变?(6)有些范畴成员可能会消失,它们是如何消失的,消失之后对其他范畴成员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范畴结构变化有规律可循吗?(7)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是依据家族相似性建立起来的,可不同范畴之间又是如何取得联系的?如何确定相关范畴之间的重叠程度?(8)各语言都有很多同义词,它们是否同属一个范畴?但按照一个词项就是一个范畴来说,它们又应当属于不同范畴,这该如何统一起来。一般说来,同义词的中心意义基本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可能存在有同中心成员(原型)的不同范畴,这该如何解释?
4.范畴容忍度问题
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可知,处于范畴中心的原型成员应具有最大范畴信息量,只有边缘成员才可能与其它范畴的成员相融合,而原型成员仍然是明显可辨的。但over具有属性“垂直、不接触”的意义,不管将哪一项作为原型成员,都与“above”的中心意义(也具有垂直、不接触的属性)相重合,确实在使用中这两个词在很多场合中是可以互换使用的。这岂不是在说:一个范畴的原型成员可能与其它范畴的原型成员相融合,这就与上述的观点相矛盾!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否应将over和above视为同一范畴?根据家族相似性理论可知,意义相差很远的义项不可能被置于同一范畴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开始研究范畴扩展过程中的“扩展限制”问题,如何不至于将毫无相干的意义放到同一个范畴中来,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范畴容忍度问题。Pulman(1983:73)认为,可以十分安全地作出假设:没有一个语言有一个词项同时能表示下面三个义项:茶杯、糖浆、噪音。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英语单词buff确实可表示很多毫不相关的意义:polishing pads, yellow colour, amateur enthusiasts。另外,相反的义项一般说来不可能置于同一范畴中,在语言表达中用一个单词来表示,可是在自然语言中就偏偏存在这样的情况,如:sanction(批准,授权,支持;也可意为:制裁,禁止船出入港口),overlook(检查,监督;也可意为:看漏、忽视)。汉语中也有近百个反义同词,例略。原型范畴理论似乎对此尚未作出合理解释。
5.概念的体验性问题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们的基本概念来自感知体验,主要来自人们对身体和空间的认识,但有些学者,如Piaget(1961),Smith et al(1999),Perner(1991),Flavell(1988),Wellman(1990),Rakova(2002)等认为: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与身体和空间有关,例如儿童什么时候才开始认识到可将自己的身体,外部的物理环境,以及视野看作容器?什么时候才能比较稳定地理解三维空间?构成容器(内部、外部、边界等)和三维空间(长、宽、高等)的要素有那些?就我们的直觉而言,较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要素还是需要一定智力基础的,儿童早期似乎还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认识出现得较晚,那么它们又何以能成为形成基本概念的基础呢?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有些基本概念是否与感知体验同时形成,或在其后形成?对抽象性意义的理解难道一定是基于对体验性意义的理解(Asch & Nerlove:1960)?某一抽象性意义(如:专政、制度等)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体验性意义?人们的抽象性意义难道都是基于体验性概念通过隐喻建立起来的?人类的逻辑推理难道也一定是基于感知体验的吗?学者们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证明,体验哲学的解释力受到了挑战。
6.隐喻问题
认知语言学家将隐喻置于显赫的地位,但这一理论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作出统一解释。
(1)隐喻的作用。认知语言学家将隐喻视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人们不禁会问:隐喻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就连L & J也没能对其作出一个统一的说明(参见王寅,2001:314)。
(2)隐喻的体验性。L & J强调了隐喻的体验性,隐喻植根于体验,而我们发现许多隐喻却不一定是以体验为基础的。就“是牢笼”这一隐喻而言,没有结过婚的人,没有蹲过监狱的人,同样也能理解这个隐喻的意义。如是说可通过间接经验理解,那么间接的程度该多大呢?
(3)根隐喻的普遍性。人类的体验有很大的共同性,如我们都有“看”的能力和经验,但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将“看”与“知”联系起来,形成所谓基础性的“seeing-to-knowing”推理。据Rakova(2002:224)介绍,在芬兰语中就没有这样的隐喻,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为什么有的语言能形成上一隐喻,而有些语言却没有,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将这一隐喻视为基本隐喻,如果基本隐喻不具有普遍性,那么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隐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体验性?”
(4)隐喻与相似性。既然强调了隐喻的体验性,就不该否认隐喻是基于对相似性感知之上的观点,而他们反复否认这一观点(Neisser:2001),过分强调隐喻可以创造相似性,这也是不很全面的。我们认为:一方面隐喻是基于对事物、行为、现象等之间相似性的感知,这是隐喻的体验观,认知模型、意象图式、常规关系对其具有解释力;另一方面隐喻也可以创造相似性,如独特的诗句确实可以使得人们认识到一些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此时常规关系的解释力就有限了。强调任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因此,相似性和隐喻两者之间具有一种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
(5)本体与喻体的互动性。在隐喻的理解过程中,喻体将其某一或部分属性(不可能是全部,也不可能是一点不变的)映射到本体上,使本体也具有同样的属性。因此本体在接受映射时,就必然要对喻体的属性作出选择和限制,例如在隐喻:“He is a mule.”中,“mule”有很多属性,仅将其中的一个属性“倔强性”映射到了“他”上,而排斥了许多其它属性和特点:动物、长耳朵、吃草、可骑、埋头拉磨,等。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人们是如何限制“mule”的其它属性和特征,而仅将“倔强性”挑选出来的?其挑选的依据是什么?这在他们的隐喻认知理论中语焉不详。
(6)隐喻的认知机制。L & J的隐喻认知理论主要强调了始源域向目的域的映射,但笔者(2003)认为对隐喻的理解需要五个因素:认知主体、本体、喻体、喻底、语境,缺一不可,它们都对隐喻的生成和理解起作用。本体是隐喻所要描述的对象,对隐喻的理解显然要提供一些已知信息,如在“He is mule”中,倘若换了本体“He”,则会影响到对“mule”(该词除“笨蛋”之外还可指:杂交种动物,杂交种植物、纺织机、小型拖拉机等)属性的选择。认知主体对于隐喻的使用和理解所起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会创造出不同的隐喻,即使同一语言社团中的人,因其背景不同对同一隐喻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就涉及到语境因素,其对隐喻理解也可起到制约作用,这在他们的隐喻认知理论中未加论述。如有的喻体具有多层含义,这就需要依靠语境来确定隐喻的意义。
(7)隐喻与哲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哲学教授Neisser在“Language”2001年第一期上对L & J于1999年合作出版的专著发表评论文章时指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根隐喻”上,大部分认知可被理解为是这些根隐喻的表层反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的哲学理论就是建构在几条根隐喻之上的,这就将哲学史视作隐喻史了,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批判了历史上的哲学家没能认识到其理论的隐喻性,这显然缺乏充足的说服力。他还指出:倘若把隐喻视为基本的、主要的认知工具,可不断创造新的意义,这是否就会将隐喻视为一种计算工具,这又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有意义的活动行为才能产生意义”的观点相悖,似乎就与心智的体验性原则相矛盾?Rakova(2002),Sapiro等(1989)也对“It is metaphorical thought that makes scientific theorizing possible. 提出了疑问。
(8)隐喻与换喻。“隐喻”既可作广义理解,换喻为隐喻的一种形式,又可作为与隐喻平行的单独一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互动关系;还有学者认为两者是一个连续体(Radden:2000),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Goosens(1995)则认为隐喻中可能包含换喻,换喻中可能包含隐喻,如:pay lip service to the project(对该项目仅表示口头支持,而不给经费)这是一条包括隐喻的换喻,pay表明一个财务场景,该场景相关事情有邻近关系,可视为换喻,而lip service为“口头服务”,来表示“不给经费”则具有隐喻性。 我们知道,隐喻常被理解成是发生在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换喻常被理解成是发生在同一个概念域之内的映射,现将上述对隐喻和换喻的理解划图如下:
隐 喻 换 喻
关于同一概念域和两个概念域有时是很难划分的,即使将这里的“概念域”说成是“基本概念域”,这也是个笼统的说法,究竟“基本”到什么程度。概念具有上下义层级性,在右图的换喻模式中,方框可被视为一个概念域,其中有A和B两项,如果我们能在左图为两个概念域找到一个上义性概念域,此时划分隐喻和换喻就难免会产生困难,
A: How did you get here? B: I have got a car.
用原因“我有车”来表示结果,可视为换喻,因为原因与结果是一个整体事件的两个邻近概念。当然我们也可将原因与结果当作两个不同的概念来处理,此时就是隐喻。又例:He is in low spirits. 常被视为隐喻,但我们也能找出一个上义性概念域来对其作出换喻性解释:
情感域
悲伤 高兴 ……
面部 体态 言语 ……
不悦 下垂 低调
此时就可有两种解释:(1)作为隐喻解释:悲伤为上义概念,其下义概念或情况可包括:面部不悦,身体姿势下垂,言语低调…,用low的身体姿势来表示悲伤,实际上就是用下义概念来表示上义概念,形成了跨域用法,当算隐喻用法。(2)作为换喻解释:在悲伤这个概念域中可包括:面部不悦,身体姿势下垂,言语低调等,这也可视为同一概念域中的用法,悲伤时会有一系列的表现,体态下垂仅是其中之一,用部分表示整体,当算换喻。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又该如何解释呢?认知语言学家似乎还没有说清楚。
7.主观性问题
认知语言学强调主客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主观色彩。Johnson(1987:174)似乎也曾为此辩解过,他强调了意义是基于对共同世界的经验之上形成的,因此意象图式和隐喻虽然具有想像性,但也具有体验性,是人们所共享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Sweetser(1990:13)也曾说过:体验主义比起客观主义来说,主观性更少,因为前者致在解释人类语言和认知的实际范畴,而客观主义预设了一个十分武断的命题:语言范畴一定具有客观基础,同时还假设客观的真实世界必须是像语言一样建构起来的。但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分析方法确实存在着不少主观性,如确定一个语言形式的意义需要依赖百科知识,可如何确定与之相关的知识呢?Neubauer & Petöfi曾对“氯”所作的综合语义分析可谓十分全面(参见李幼蒸,1999:307):化学特征、物理特征、生物特征、还涉及到地质、历史、词源、生产、用途、储存等一系列知识,我们什么时候按专业知识理解,按哪个专业理解,似乎无法确定,对于普通人来说,其中大部分内容好像都很陌生。
联想论、激活论对语义所作的解释也是模糊的,一个词究竟能引起哪些联想,激活哪些概念,倘若这个问题答不清楚,说明一个词的意义是难以确定的。另外,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语会有不同的联想,经验、背景、年龄和地域的差别,往往会对同一个词语会产生较大差异的联想。如此说来,人类又是如何进行交际的?仅用原型理论、认知模型、意象图式能否对其作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
因此,我们认为传统的语义特征分析方法并不是一无是处,对主要特征进行简单明了的描写,从语言内部的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上来刻画语言形式的意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能将传统的语义方法与认知语义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则会对语义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另外,认知语法中在作词类划分时,主张用识解(意象),特别是突显,来作为判断标准,这里仍旧涉及到主观因素问题,究竟以谁的“突显”为标准。另外,他一方面主张用突显而不用概念来划分词类,但他区分名词和动词时用了“Thing”和“Relation”,这能算是不用概念吗?他还用“有界-无界”来解释名词的可数性,用动态和静态来解释词类转换,那么他说的“有界-无界”、“动态-静态”难道不属于“概念”?离开“概念”的分析是很难想像的,难怪Taylor(2002:179)说:Langacker在区分主要词类时还是用了概念性的定义。
8.框架和意象图式问题
框架和意象图式通常被视为某人或某社团对典型物体、事件、状态所具有的知识总和,或属性包, 它常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方式固化储存在人们的知识之中。用框架来表征知识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方便的方法(Goldstein & Roberts, 1980: 42),但人们的知识非常广泛,究竟要多少框架才能将人类知识系统描写清楚?框架系统具有层级性,同级和上下级框架之间具有什么联系,它们的关系该如何描写才能清楚?一个人同时可能会有多重身份,如张先生可能既是教授,又是系主任,还可能兼有其他职务,此时就必然要涉及到多个框架,如何处理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再例:John is a dog’s owner. 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表述, 究竟应涉及到几个框架?是在“MAN-框架”,还是在“OWNER-框架”中处理这个问题(Hayes, 1980: 50)?另外,一般说来,一个事件会包括多个相关活动(clusters of related activities),那么同时就需要数个框架来加以理解,该如何确定需要选用哪些相关框架,这些框架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描写,如何确定其间的联系,靠逻辑还是靠分类,还是其他什么?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会有很多这类多重现象,框架理论又该如何处理呢?人们是如何选择有关框架相互理解呢?人与人之间所认识到的框架是有差异的,那么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缺省值(Default Values)也就会有差异,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另外,“脚本”被视为框架或图式之一种,它是一种共有信息的原型代表,其内部所含信息往往呈有序排列,是一种经常发生、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框架或图式。如常说的餐馆脚本,包含了一系列的因素。这一理论对于分析典型的日常事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样也有一些不足之处:(1)生活中常常有许多非典型事件,很难用一种固定的“脚本”作出圆满的解释,对于那些经常不按常规办事的人说又该怎么办?(2)现实中会存在很多难以界定的各种事件,究竟可划归到哪一种“脚本”中来理解,这也可能又是一个未知数。(3)难道每个事件都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脚本”?我们究竟能列出多少“脚本”出来,这同样也面临着像很难列全语义成分一样的难题。(4)在很多情况下,理解一个事件需要很多脚本,如何确定这些脚本以及其间的联系,究竟需要哪些相关脚本,排除哪些不相关脚本,而且还涉及到在哪个时刻需要选用哪个脚本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心智过程,该理论也未能提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到1980年为止SAM (Script Applier Mechanism) 才有20个脚本,关于描写故事的才有6个脚本(Lehnert, 1980: 93),这对于描写人类的知识可谓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 (5)“脚本”是经验化的结果,其形式会随着人的经验增加而不断完善、修正,但何时才能算是形成了一个典型图式?在人们尚未形成该典型之前又该如何描写这种知识呢?我们虽然可用动态观点来加以解释,这里仍未能摆脱不确定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其推到认知的灵活性、多变性的范围里,又总让人有一种言犹未尽的感觉,理论的可靠性似乎难以得到保证。
在语言理论研究中我们不可割断历史,认知语言学是在借鉴最新哲学观点和对以往语言理论深刻反思,乃至挑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在很多方面相对其他学派确实具有较大的解释力,但其本身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不能期望认知语言学能解决语言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语言探索尚未成功,广大同志仍需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地认真思考,深入研究,继承认知语言学中的合理部分,发展其尚未阐述清楚的地方,更正其不足之处,才能使得认知语言学更趋完善,走向完美。同时,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还要进一步将英汉语结合起来研究,努力把我们的成果运用于语言教学,介绍和推向西方,将其融入到21世纪东学西渐的潮流之中,这样才能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语言学。
笔者仅从自己的学习和思考中略述管见,指出认知语言学中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引起同人的注意,衷心期望大家能不断完善认知语言学,或在此基础上再向前走,建立更有解释力的新理论,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境界:
继往开来,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发展语言理论,有所建树;
承前启后,让后来者能踏着我们的肩膀奋力向上攀登,超越我们!
主要参考书目: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王 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Asch, S. E. & H. Nerlove. The Development of Double Function Terms in Children[A]. In Kaplan, Bernard and Seymour Wapner(eds.).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ical Theory[C].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0.
Flavell, J. H.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Knowledge about the Mind: From Cognitive Connections to Mental Representations[A]. In Astington W. etc.(eds.), Developing Theories of Mind[C]. CUP, 1988.
Goldstein, I. P. & R. B. Roberts. NUDGE, a Knowledge-based Scheduling Program[A]. In D. Metzing (ed.). Frame Conceptions and Text Understanding[C].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1980.
Hayes, P. J. The Logic of Frames[A]. In D. Metzing (ed.). Frame Conceptions and Text Understanding[A].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0.
Lakoff &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Lakoff, G. &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Lehnert, W. G. The Role of Scripts in Understanding[A]. In D. Metzing (ed.). Frame Conceptions and Text Understanding[C].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0.
Neisser, J. U. Book Review 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J]. Language, 2001(77).
Perner, Josef. Understanding 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Piaget, Jean. The Mechanisms of Perception[M]. Translated by G. N. Seagri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1.
Pulman, S. G. Word Meaning and Belief[M]. London: Croom Helm, 1983.
Rakova, Marina. 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 a High Price to Pay?[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2 (13-3).
Sapiro, Rand. J. etc. Multiple Analogies for Complex Concepts: Antidotes for Analogy-induced Misconception in Advanced Knowledge Acquisition[A]. In Vosniadou, S. and A. Ortony (eds.), Similarity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C]. CUP, 1989.
Smith, L. B. etc. Knowing in the Context of Acting: The Task Dynamics of the A-not-B Error[J]. Psychological Review,1999( 106).
Sweetser, Eve Eliot.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 Metaphorical and Evolution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M]. CUP, 1990.
Taylor,Joh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Theory[M]. OUP, 1989.
Wellman, H. M. The Child’s Theory of Mind[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