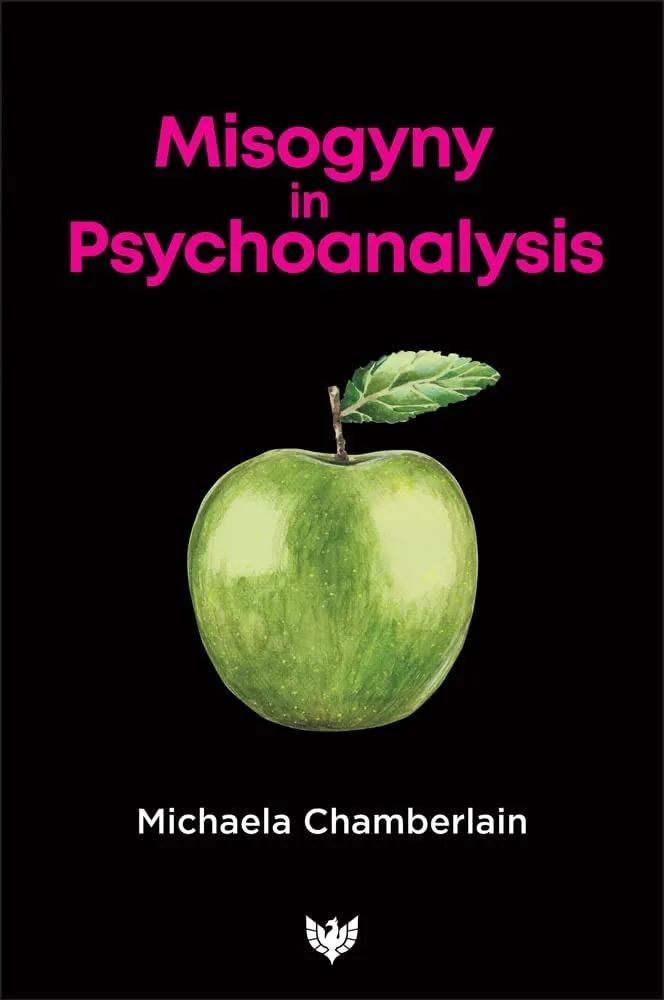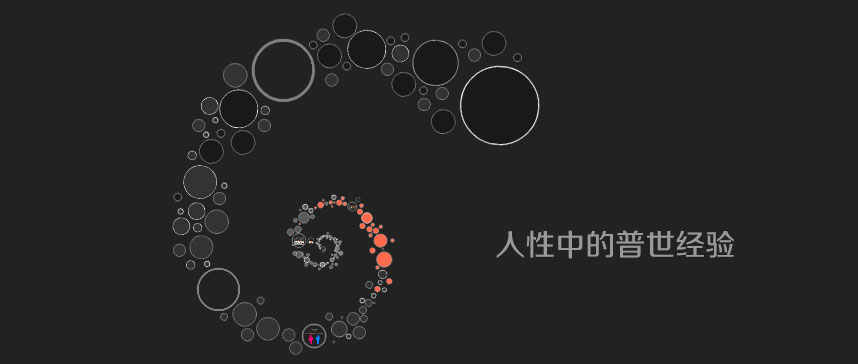柏拉图、休谟和杰弗逊都试图弄明白人类的心理构造,但他们手中都没有一个用以阐释生物构造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即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痴迷于,任何生物间合作的例子都要用他一贯强调的竞争和“适者生存” [5] 理论来解释。对于道德可能是如何进化的,达尔文提供了几种解释,其中大多涉及诸如同情之类的,他认为这些情感是人类社会本能的“基石”。他也写到了羞耻感和荣誉感,它们与人们对声望的追求相关。达尔文是道德先天论者:他认为自然选择赋予了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
然而,社会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受到了两波道德主义的影响,先天主义因此成了一种道德冒犯。第一波是人类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恐惧,这一主义由达尔文提出,但他并未支持它。其大意是,最富有、成功的国家、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适者”。因此,向弱者施与宽仁救济,使之能繁衍下去,就等于是干涉了自然进化的过程。 [6] 某些种族天生就优越于其他种族,这一说法后来受到了希特勒的拥护。如果希特勒是先天主义者,那么所有先天主义者都是纳粹分子。(这个结论的逻辑有误,但如果你不喜欢先天主义,这样说就很过瘾。)
第二波道德主义是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卷席美国、欧洲和拉美的激进政治。激进的改革者们通常相信,人性是一块白板,在上面可以绘就任何乌托邦图景。比如,如果进化赋予男人和女人不同的需求和技能,那么想要在很多职业中达到两性平等就存在困难。如果先天主义可用来为既存的权力结构辩护,那么先天主义就是错误的。(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逻辑错误,但正义之心就是这么运作的。)
20世纪70年代的哈佛研究生、家史蒂芬· 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2002年的著作《白板说:对人性的现代否抑》(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里描述了科学家们如何背叛科学价值以忠诚于进步运动。科学家们在演讲厅里都变成了“道德表现癖患者”,他们妖魔化自己的同事,还要求学生们将是否与种族、性别平等等进步论调相一致作为评价各种思想的标准,而不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
对科学的背叛在对爱德华· 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攻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人终生致力于研究蚂蚁和生态系统,1975年他出版了《生物社会学:新的综合体》(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一书,该书探讨了塑造动物形态的自然选择(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怎样同时也塑造了动物的行为。这个观点本不具争议性,但是威尔逊在最后一章大胆地宣称,自然选择同样影响了人类行为。他相信,所谓人类天性是存在的,它划定了我们在抚养后代和设计新的社会制度时所能达到的界线。
威尔逊用伦理学来阐释他的观点。和劳伦斯· 科尔伯格以及哲学家约翰· 罗尔斯(John Rawls) [7] 一样,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因此,他相当熟悉后两者着力论述的权利和正义的理性主义标牌。威尔逊心中清楚,进化是道德的最佳解释,而理性主义者实际做的则是为道德直觉创造巧妙的正当理由。大家相信人权是因为这东西像数学定理一样真正存在吗?它正陈列在宇宙货架上,挨着毕达哥拉斯定理,等待柏拉图式的理性者去发现?还是只因为人们在读到对酷刑的记述时感觉到憎恶和同情,所以才发明了一个关于普遍权利的说法以将这种情感正当化?
威尔逊和休谟站在一边。他指控道,在“请教自己大脑的情感中心”后,道德哲学家们实际上在做的是捏造理由。 [8] 他预言,哲学家很快就会失去伦理学研究,这一研究将“生物学化”,或将发生改变以适应关于人类天性的新兴科学。哲学、生物学和进化之间的联结便是威尔逊设想的“新综合体”之一例。他后来使用“协调体”这一说法,即各种观念杂烩,造就知识的统一体。
先知们对现状的质疑经常会招致掌权者的仇恨。这样说来,威尔逊应当被称为道德心理学的一个先知,他在刊物上和在公共场合中都遭到憎恨和谴责。 [9] 威尔逊被称为法西斯分子,这一称呼令(有些人)对他的种族主义指控,以及(有些人)禁止他公开发表言论的行为具有了正当性。抗议者们打断威尔逊的科学演讲,冲上讲台呼喊道:“法西斯分子威尔逊,你躲不了的,我们以种族屠杀罪指控你。”
www.nmgpsy.com内蒙古心理网[5] 这个著名的术语是赫伯特 ·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首创的,但达尔文也使用过。
[6] 这一观点是赫伯特 · 斯宾塞在19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但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托马斯 ·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达尔文确实认为部落之间存在竞争(见第9章),但他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7] 罗尔斯至今仍是最经常被引用的政治哲学家,因其1971年的著作中的思想实验而闻名。他让人们设想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设计这个社会,也就是在事先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社会中占据什么位置的情况下看人们会怎么设计这个社会。理性主义者倾向于喜欢罗尔斯。
[8] 威尔逊的原话太有预见性了,准确到令人难以相信:“伦理学家们通过请教自己大脑的情感中心直觉式地知晓了道德的义务性准则。这也适用于发展主义者(比如科尔伯格),尽管他们已经尽力做到客观。只有将情感中心的活动看作是生物学上的适应,才能破译这些准则。”
[9] 一些著名的生物学家如史蒂芬 · 杰伊 · 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理查德 · 雷威丁(Richard Lewontin)都写文章嘲讽生物社会学,反对其将科学与社会正义的政治议题联系到一起。